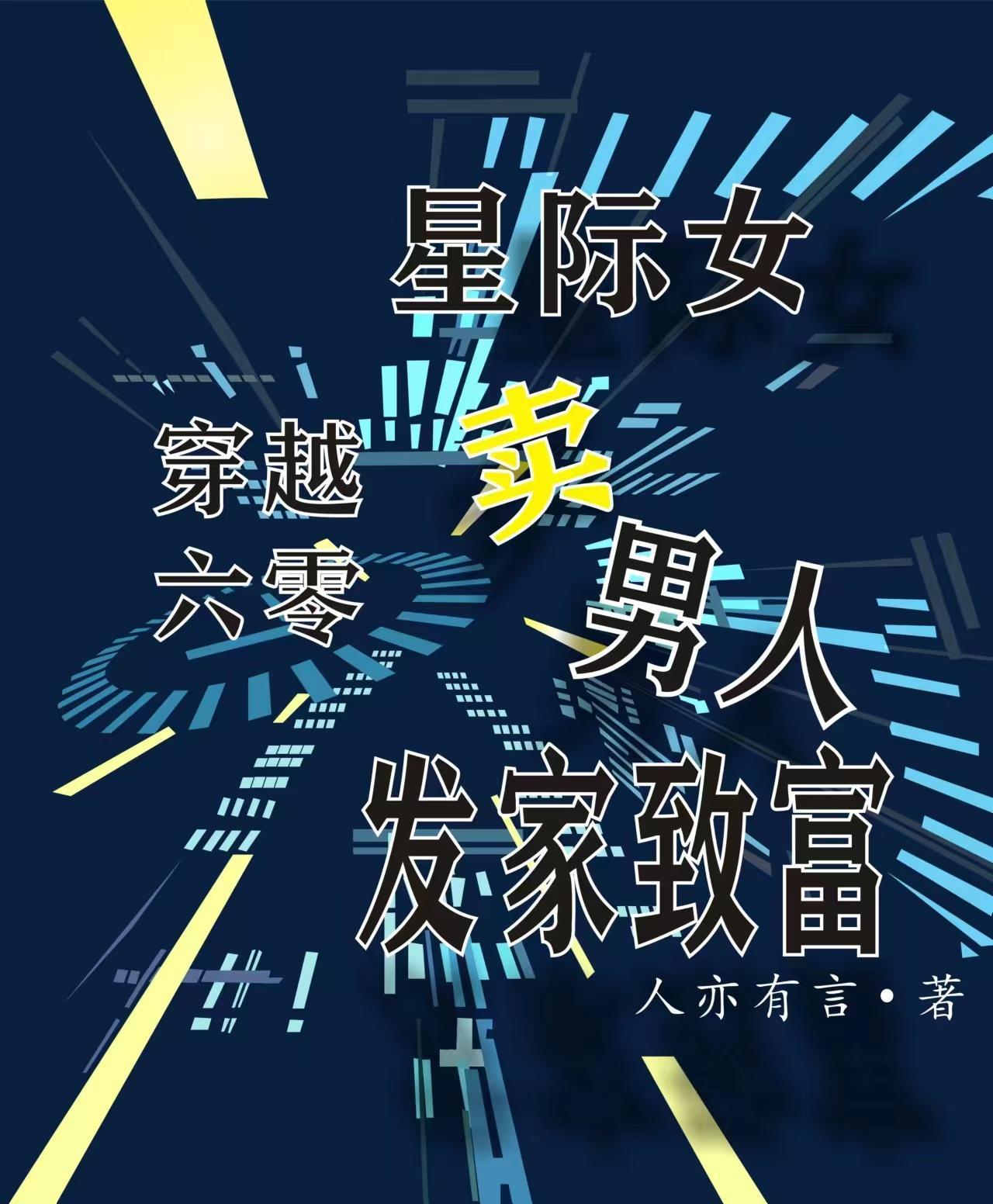看书阁>女子虎豹巡护队 > 第98章 克星(第2页)
第98章 克星(第2页)
窦红英见状,又拿了一袋奶,撕开,递给葛勇。
葛勇回到家的时候已经9点15分,钱舒静还没回来。他烧了壶水,洗脚洗袜子。
洗完脚,他端起洗脚盆出门倒洗脚水,回来后感觉屋里缺了点什么,怎么这么静呢?
缺了点什么呢?噢,他终于想起来了,花猫不知跑到哪去了。
“喵,喵。”他唤了两声,花猫没有回应。他想,也许花猫饿极了,跑到外面找吃的去了。
他看了会儿电视,躺在沙上迷迷糊糊睡着了。
屋门不知啥时打开,把睡梦中的葛勇弄醒。
“老公,老公,你快起来。”钱舒静抑制不住一脸的兴奋,大呼小叫。
葛勇睡眼惺忪坐起来,看墙上挂钟,已是深夜11点2o分。
“你瘾头咋这么大呢,都几点了,才散场。”葛勇打个哈欠,准备上炕睡觉。
“老公,你说神奇不神奇?”钱舒静一把扯住他胳膊,兴奋地说,“今天我抱着花猫去打麻将,赢了,那点子,兴极了!”
钱舒静说完,在花猫脑袋上亲了一口,花猫大概累了,懒散地“喵”了一声,从她怀里蹿下来,跳上炕,在炕头上趴下了。
“打麻将就打麻将,你说你,抱着个猫去打麻将,也不嫌烦。”葛勇不耐烦地甩开钱舒静的胳膊。
“烦啥烦啊,‘大赢’可是我的财神爷,我恨不得打个板把它供起来,哪能烦它呢,是吧‘大赢’。”
钱舒静从包里掏出一根火腿肠,撕开**,掰成一小段一小段,去炕上喂猫。
“你是不是输钱输蒙圈了,花猫还成了你的财神爷,病得不轻!”葛勇嫌弃地白了她一眼,上炕钻进被窝。
“这你就不懂了,咱家‘大赢’真是财神爷,不骗你。”钱舒静专心喂猫。
“什么‘大赢’?谁啊?”葛勇被她弄得脑子乱糟糟的,傻傻地看着钱舒静。
“花猫啊,”钱舒静把身子转向葛勇,“我说我怎么老是输钱呢,早晨有个算卦的瞎子从咱家门口路过,我求他给我算一卦,他说我的名字不好,钱舒静,不就是‘钱输净’的意思吗?哎妈呀,我才恍然大悟,可不呗,瞎子说的太有道理了。”
“所以,你没法改名字,就管花猫叫‘大赢’,希望你打麻将大赢是吧?”葛勇讥讽道。
“是啊,所以我今天就抱着‘大赢’去打麻将,果真就赢了,大赢,你说邪乎不?”钱舒静神神叨叨地说。
“那你得去找你父母算账,问他们为啥给你起名叫钱舒静,而不叫钱大赢?”葛勇钻回被窝,蒙上了脑袋。
“废话!我找他们,他们早就是地下工作者了,我是土行孙啊?”钱舒静因为赢钱,情绪很好,就没生气。
“我就不信那一套,你那是封建迷信。”葛勇蒙着脑袋,瓮声瓮气地说。
“死犟眼子,”钱舒静说,“有些事你必须得信,不信都不行!”
葛勇把蒙住脑袋的被子掀开,“你还别说,我以前听说,县城有个赌徒,赌钱总是输,他就在屁股上纹了几只苍蝇。有一天他去浴池洗澡,搓澡的看见他屁股上纹着些苍蝇,就问他,纹啥不好,干嘛纹些苍蝇呢?”
“为啥呀?”钱舒静来了兴致,屁股挪过来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