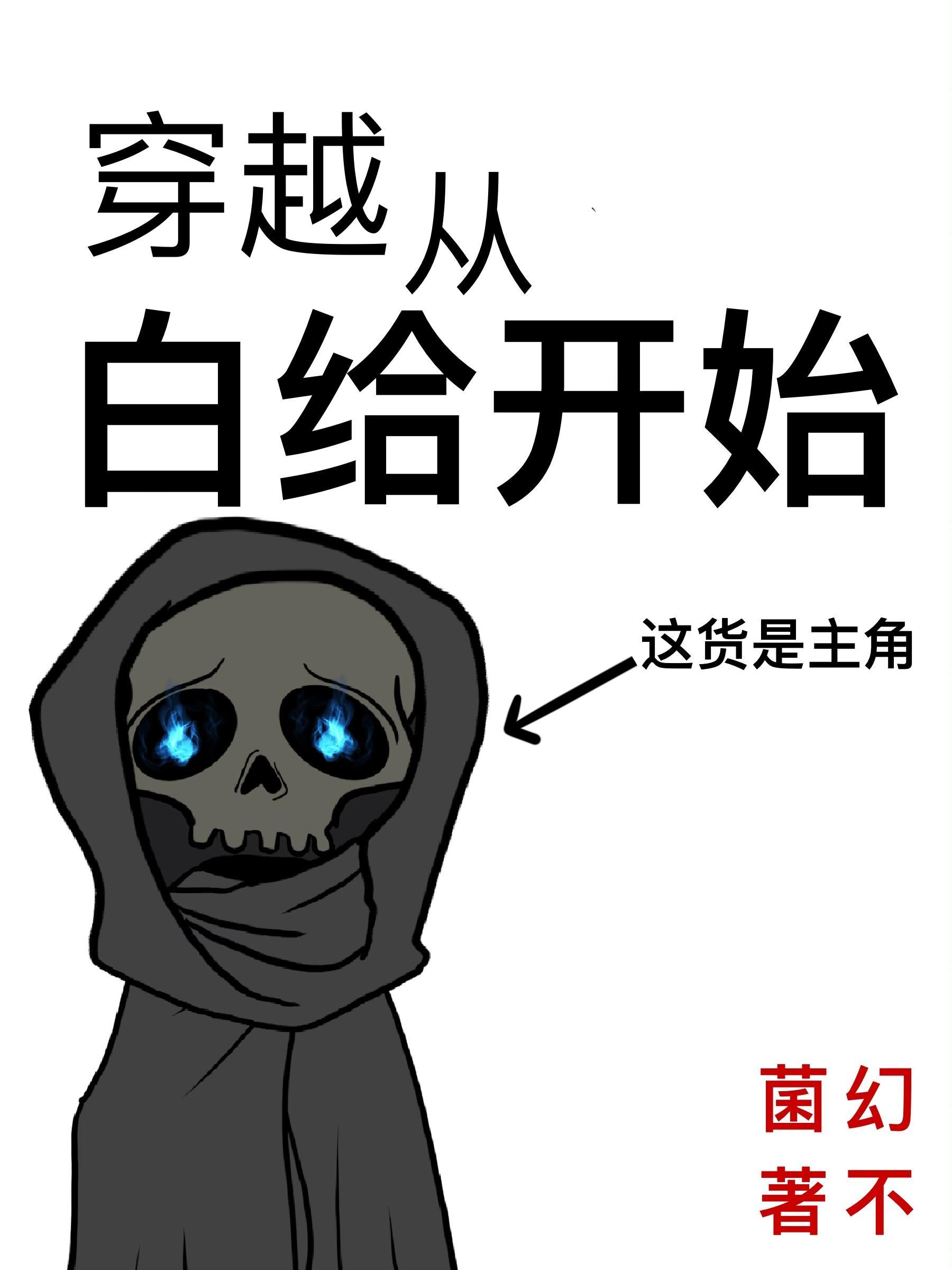看书阁>穿越宋末,从琼崖崛起 > 第113章 治理广州(第1页)
第113章 治理广州(第1页)
刘成勇撤走的第二天,贺州下了一场冬雨,绵延的山火被雨水浇灭。
蒙鞑的士卒清理了半日才开辟了道路,只是这山间一下雨,路就更难走了。等阿术的两万多大军又花了三日来到临贺之时,临贺已经是一座空城,能跑的全跑没影了。四处搜寻抓到了几个本地人才知道,这五千宋军已经向连州逃窜。
这城里总共也没多少人,阿术也无心屠城了,在临贺休整了两日,四处征了些粮草跟着刘成勇的踪迹便追了去。那五雷炮阿术是定不能放过的,至于收复各州县,留给阿里海牙去做也就是了。
刘成勇还在往阳山奔袭,试图在阳山吸纳义军,依托山势再阻击阿术。
一生谨慎的范文虎范大都督此刻已经从英德府征到了马匹,又顺着翁水,快要赶到了翁源。文虎大都督虽是吃了败仗手中只有几条小战船,可这日夜兼程的行军度放眼天下那是无人能及。
隔日,原本打算继续沿水路去龙南的范大都督,到了翁源听闻南雄州、韶州正被多股义军攻打,想想江西道的龙南怕也不保险。范大都督便舍了船只,骑着马往循州龙川方向而去,打算经梅州往福建路奔逃,到了泉州问蒲寿庚要几条船再回两浙。虽然绕了点路,就当是巡视天下了。
广州南海县的军营里,江钲正望着阶下跪着的朱胜、厉德彪和王国佐三人,三人的伤势倒是被治得七七八八了,虽然有些病恹恹的,显然死是死不掉了。
“江大人,冤枉啊!”朱胜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地跪在那里哭嚎:“予乃老臣,原本在湍滩亦是死战不退的,可那日范文虎率部临阵脱逃,致我等落于阿术罕之手,并非予愿降蒙啊!末将这十几年来忍辱负重、虚与委蛇就是为了有朝一日能报效朝廷。那日在零丁洋上,我部一箭未,望王旗所至便归于麾下,哪里来的叛逆之说。予之赤胆忠心,日月可鉴,天地可证。”
厉德彪和王国佐一听更是急了,这话都被你说完了,我俩不就死定了?纷纷叫道:“我等也是冤枉的啊!范文虎以我等家眷胁迫,无奈之下才纵舟前来。可那火舟被我等早早点燃,是伤不到王师分毫的。出之时我二人便商议好了弃暗投明,和王师一起光复河山驱逐鞑虏。我等亦是一箭未,怎不算以军而降。望江大人明鉴。”
“你这颠倒黑白的狗才!”朱胜是恨死这两个了,破口骂道:“你二人纵火船,就是逼迫我与王师对战,陷我于不仁不义之地!”
“你休要血口喷人!”
“什么一箭未,几里之外你射得到吗?”
“你何尝不是如此。”
……
“够了!这里不是蒙元,我又不是你爹爹,叫的甚大人!”江钲猛地一拍桌子:“官家说了尔等就是心中没有这华夏异族之分,才会误入歧途,也相信尔等乃不得已而降,既非主犯不会要尔等性命。这伤也给尔等治了,这头颅也留在尔等项上,只是厮们所谓的望王旗而降之事休要再提,留几分颜面做人吧!”
江钲继续说道:“今日提尔等来此,便是告诫尔等莫要胡思乱想坏了自家性命。这性命虽是保住了,总要谨言慎行。官家说了,尔等先去怀圣寺养伤思过吧。”
“来人,带走。”
三个人也顾不得脸面,趴在地上,高叫道:“谢官家恩赏。”。几个士卒走了进来把这仨架走了。江钲望着离去的三人不禁摇头叹息。
这几日赵昰一直和几位大臣商讨着如何处置这三人。凌震的意思,既然曾是叛将,就当也绑去路口让民众泄愤。可王应麟、江钲是坚决不同意的,这几个都是被长官卖了才落入蒙元之手,哪怕是贪生怕死也是情有可原,更何况无论如何现在都是归降的,这一杀以后怕是没人愿降了。
考虑再三赵昰也就留下这三人的性命,若是表现不好将来再翻老账便是了,这种人无足轻重给个无差遣的寄禄官职都是可以的,暂时先关到庙里,做个标杆算了。
南海县外烧成白地的元军营寨已被清理干净,这次进攻广州俘获的七万余士卒,除了长了张挖矿脸的都在这了。一些实在是不适合继续当兵的,比如五十多的,缺胳膊少腿的,都被遣散回乡了,路途遥远的便送去琼崖,让他们开荒种地或是新城务工去了。
剩下的六万余人,日日除了劳作操练,便是听故事、搞批斗、齐诉苦,日子倒也是充实满足。幸好南海县里有范大都督运来的十二万石(72oo多吨)粮食,也能让这些新兵吃上一干一稀。
琼崖的镇海号王船业已出,载满了将要送给忽必烈的礼物在海上龟前行,负责押运的是白沙水寨的郑凯和神火司的陈惟中。现在进入冬季海上也无台风,更不会和元军水师遭遇,自然也行得顺畅,无非是度太慢了些罢了。
建造新的联合工厂位置赵昰已经看好,就设在西城外靠近珠江口处。原先的庄户地主得了朝廷按市价给的补偿,不吵不闹地走了。拆迁工作没有任何阻力,等三天之后人都搬走了,那七万新兵便要派来此处劳作了。烧窑的炼铁的工匠广州更多,只等把土地整理了,便能搭起轮窑高炉,无非是把海口的再复制一遍罢了。
至于福建路江南西路等地会不会有元军来攻,赵昰是不担心的,这年代通讯手段和运输手段如此单一,等忽必烈调动大军筹集粮草结束,他早就打到泉州去了。
赵昰暗自喜欢这时代的工作效率,如此大规模的拆迁在后世没有个一两年搞不定,自己不过几日便做成了,果然是王者风范最好用了。
收缴的船只还在维修,只等琼崖运来火炮便可整装启航,沿潮阳(今汕头地区)一路打上泉州、福州。
这广州光复之后也有些原本避难隐居的宋朝官员相继找了过来,其中最着名的便是那赵昰亲封的江东制置使也就是《蚕妇吟》的作者谢枋得(这个枋字以前在这里是读柄的)。
这谢枋得兵败之后流落到建阳,隐姓埋名做了个算命先生。以此谋生,困顿异常。有一日听闻说是朝廷现在落在琼崖,张弘范前去讨伐五百舟楫六万士卒全军覆没,便起了想去琼崖找寻的念头。一路从福建走到了惠州,在惠州又听闻王师光复了广州,便想来广州寻找。
奈何这一路说好听点是风餐露宿,说实在点便是乞讨,是吃尽了人间的苦楚。这衣服也磨烂了,鞋也走破了,一身打扮和个乞丐没有两样,终究是无力再走了。在博罗又是赌咒又是许诺地央求了几日,才有一条疍船肯搭他来广州。
赵昰对于这位顾大义不计荣辱,守操节以死明志,历经磨难,生死不改,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文人,自然是万分的佩服的。赵昰虽然没有研读过《演员的自我修养》,但是有过凌震那次的经历,这抱头痛哭之事是随手沾来。于是乎,君臣二人抱头痛哭了一场,那凌震得知了消息也赶了过来,三人又哭了一场。
等哭不动了,赵昰便着人领着谢枋得去沐浴更衣治疗伤势去了。
注:宋笔记《鸡肋编》:世惟子称父为大人,若施之于他,则众骇笑之矣。又《宋史》蔡京之攸,握其父手曰:大人脉势舒缓,体中得无不适?又有柳宗元称刘禹锡母亲:“无辞以白其大人。”类似的例证比比皆是,唐宋以来都以官位相称,无所谓大人者。大人只用在称呼叔伯父母。故清人赵翼考证曰:“觌面称大人,则始于元、明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