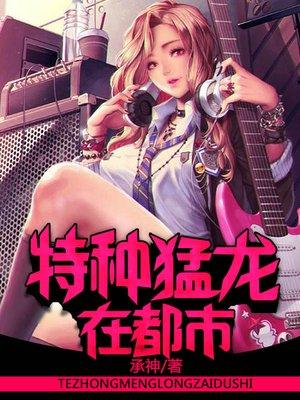看书阁>寒门升官手札 > 一更(第2页)
一更(第2页)
徐尧律没接茬,转移话题道“向棕让杂耍团的人潜伏在武英侯府,我猜他一是想盗走虎符,二是想谋害罗家,毕竟当年若不是老侯爷督帅,太子怕是就要死在关外。”
蜡烛突然燃断一根,“啪”的传出炸裂的声响,屋内的光线顿时暗淡下来,两人隐在幽幽的光线下,愈的诡异。
“有一段时间京城传出谣言,”木庄起身点亮蜡烛,揣着心思道“说向家大公子生病后性子暴戾,每回病府里都会抬出好几具尸体,有人碰巧看了一眼,都说那些个下人被打的遍体鳞伤,身上没一块好肉。”
“向棕不止身体有病,心里也有病。”徐尧律嘴角暗讽“之前谢行俭在京兆府说朱长春性格大变许是鬼上身导致,我倒觉得向棕起病来比鬼上身还可怕。”……
“向棕不止身体有病,心里也有病。”徐尧律嘴角暗讽“之前谢行俭在京兆府说朱长春性格大变许是鬼上身导致,我倒觉得向棕起病来比鬼上身还可怕。”
“无事时,向棕就像个翩翩公子,一旦事情不如他的意,他手上的血鞭从来都不是吃素的。”
徐尧律回忆道“我接触过向棕,别看他整天一副含笑无辜的样子,其实心眼贼小,遇事睚眦必报,狠起来的手段跟大理寺的一百零八式不遑多让。”
徐尧律默了默,又道“他就是一条有耐心的毒蛇,被他盯上了,都没好下场,我担心罗家”
木庄倒吸一口冷气“这都多少年过去了,他怎么还如此小肚鸡肠,罗家又不欠他更何况老侯爷当年在关外保护太子安危,是职责所在,他回来陷害老侯爷做什么”
徐尧律凝神,抚了一把疲倦的脸,起身缓声道“这事说来话长,我今晚得去一趟谢家,谢行俭是老侯爷的女婿,关系老侯爷的安危一事,想必谢行俭会瞒着你我有所动作。”
木庄利落的拦住徐尧律,打破砂锅道“向棕当年为什么要陷害太子,也就是当今皇上,他和皇上有”
“有仇。”徐尧律将手腕卷起的衣袖褪下,定定的盯着木庄,一字一句道“向棕不是向伯父的亲儿子。”
“不是向大人的亲儿子”木庄快的理清头绪,“那他是谁的儿子”
徐尧律已经快步走出了木家书房,边撑伞边交代“这事我回头和你细说,你把你手底下追踪向棕的人撤回来,我担心打草惊蛇,向棕为人阴险,他这回冒着被咱们捕捉的风险回京,肯定是有打算的,你可别乱来,他跟你丢在大理寺的囚犯可不同。”
“得嘞。”木庄见问不出什么,遂倚在门上轻笑“这事我原就不想插手,向棕是你心头的刺,抓他的活,就留给你享受吧。”
徐尧律感激一笑,撑开伞步入漆黑的雨里。
谢家。
谢行俭听罗棠笙说了些向家的事后,正准备熄灯入睡时,门外守夜的居三敲了敲门。
“小公子,徐大人来访。”居三尽量将声音压低,不过将将入睡的罗棠笙还是醒了过来。
望着坐在床上开始穿衣的男人,罗棠笙纳闷道“这都什么时辰了,徐大人来家里做什么”
谢行俭快的整理好仪容,打着哈欠用手从脸盆里舀冷水醒神。
“应该是有要事,我去看看,你先睡吧。”说完,谢行俭擦干手上的水珠,大步往外走。
主院有宴客厅,谢行俭进去时,徐尧律已经坐在里面等候。
谢行俭同样疑惑,徐大人似乎没回徐宅直接来的他家,身上的官服被雨水打湿大半,此刻正往下滴着水呢。
“居三,快给徐大人拿一套干净的衣裳”
“大晚上的,不必麻烦了。”徐尧律笑着拒绝,开门见山道“深夜来访,还请包涵,实在是有急事,不得不跑一趟。”
谢行俭闻言打起精神,凑近脑袋问道“大人所谓何事只管和下官说,下官在所不辞。”
徐尧律视线越过谢行俭投到居三身上,谢行俭摆摆手让居三先去睡,待居三走后,徐尧律紧了紧手中刚上的热茶,直言道“你府上是不是有杂耍团的下人”
谢行俭惊住,心道杂耍团的事徐大人怎么知道了。
谢行俭咽了咽口水,勉强维持住笑容,关系到田狄的生死,他只好打起马虎眼“徐大人从哪听来的消息我前段时间确实买了几个下人回家,未来家里之前,那几人是在杂耍团待过一阵子,不过早就不卖艺了。”……
谢行俭咽了咽口水,勉强维持住笑容,关系到田狄的生死,他只好打起马虎眼“徐大人从哪听来的消息我前段时间确实买了几个下人回家,未来家里之前,那几人是在杂耍团待过一阵子,不过早就不卖艺了。”
“人在哪”徐尧律冷声追问。
“大人,您这是”谢行俭故意慢吞吞道“这大晚上的,徐大人问下官家里的下人做什么”
难道都察院盯上了田狄
不应该啊,徐大人再兢兢业业,也用不着大半夜查案吧
他安排油家的去北郊教授林大山学习田狄的神态,再过几日,等林大山领悟了精髓,田狄就会安排送出京城。
林邵白白天才跟他说,已经找到合适的商队将田狄秘密送出去。
不会这么巧吧,他这边动作才刚开始,徐大人那边就有动静了
谢行俭越想越心虚,大概是因为徐大人是他老乡的缘故,每回见徐大人,他都有一种被长辈审讯的忐忑。
加之他前两年带无路引的居三去京兆府办身契被徐大人当场抓包,现在他对徐大人敏锐的观察力越的恐惧,总感觉在徐大人跟前,他像个没穿衣服的傻子。
防止被徐大人看出破绽,他抓起桌上的茶盏佯装喝水掩饰。
“才倒的热水,你也不怕烫了舌头。”徐尧律幽幽道。
“嘶”谢行俭嘴皮瞬间烫起气泡,他慌忙丢下茶盏,坐立不安的拍打身上撒到的茶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