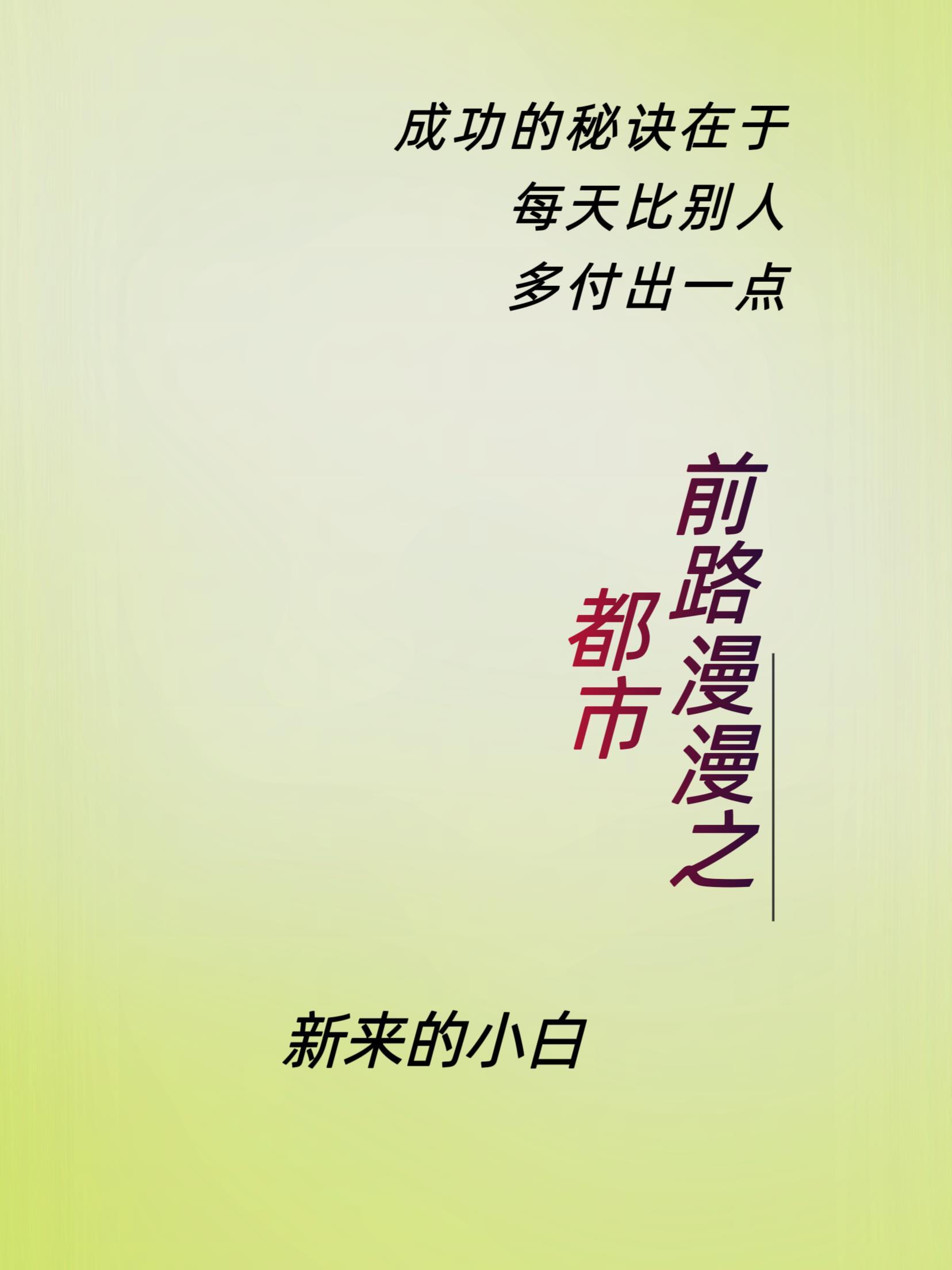看书阁>寒门升官手札 > 一更(第1页)
一更(第1页)
谢行俭一行人到达淮安城时,时间已经悄然到了十月初。
淮安城地处北界,入了十月份,整个淮安城就是双脚都踏进了冬季,呼啸的北风横刮不断,瓣大的雪花从天幕中往下直掉,转眼功夫,天地皆化成洁白之色。
进了淮安城,谢行俭率先登门拜访了上任的漕运总督袁珮袁大人。
袁珮事先接到京中来的圣旨,知晓科状元谢行俭将会代替敬元帝巡视江南府近况,因而谢行俭登门拜访时,袁珮早已用心的备下接风宴热情款待谢行俭。
谢行俭不是头一次进漕运总督府的大门,几年前因暴风雪被困在淮安城时,他曾多次被当时的漕运总督向景请到这里喝酒闲谈。
如今才过去几年而已,光景已然变换,总督不再是向景,而他也不再是那个懵懂书生。
“谢大人好生清俊有为。”
任总督大人袁珮举杯笑着称赞,寒暄道“京城盛传今年的科状元郎年少中榜,才学斐然,今日一见,果真不假,谢大人,请”
说完,一饮而尽。
谢行俭眉眼含笑,抬杯喝了一大口温酒“袁大人谬赞了,论才华,下官不及都察院的徐大人,论相貌,比不上大理寺卿木大人,惭愧惭愧,如今下官有幸能替皇上下江南巡查近况,不过是得了皇上的赏识和栽培。”
“京城佼佼者遍地开花,谢大人能从扎堆中脱颖而出,定是有过人之处。”
袁珮说话滴水不漏,谢行俭谦虚的抬出徐、木二人,袁珮能不认识这两位杰出人物吗,但今天是谢行俭的主场,袁珮这个东道主很识相的不提此二人,独独高捧谢行俭一个。
谢行俭对袁珮的赞不绝口表示一笑而过,袁珮的作为倘若放在当年,他肯定没听两句就要红脸,恨不得找个地缝钻下去。
但他在京城呆了几年,现在他的脸皮厚比城墙,这些说烂的好话,他已然是见怪不怪了。
他来之前让居三细细的打听过上任漕运总督的相关信息,一打听吓一跳,袁珮今年竟然才三十四
要知道漕运总督是肥水差事,任期只有三年,上任的人多是皇帝手底下的大功臣,这些功臣行犬马之劳大半辈子,皇上体恤其劳苦,这才安排他们来漕运当几年官。
目的就一个捞点银子花花。
漕运总督是朝廷中唯一一个被朝廷允许在任期间能明目张胆收取贿赂的官位,所谓的养廉银,每年高达几万两,这还不包括每年江湖帮派给的孝敬银。
他之所一惊讶袁珮能当上漕运总督,除了岁数太过年轻,另有一个原因,那就是袁珮是个独臂残缺之人。
和杨过有的一拼。
朝廷官员一向讲究容貌神清骨秀,从科举考试严厉审查读书人长相就能看出来,朝廷对官员这方面的要求挺严格的。
纵观朝野上下,几乎没有歪瓜裂枣,即便有,这些人肯定早就被丢到清贫偏僻之地去了。
在他很小的时候,林邵白私底下就跟他调侃过韩夫子,说韩夫子才华横溢却只能外放七品县令,大抵是输在容貌上了。
那时候他还不愿相信,可当他正经入朝为官后,才现皇家看中容貌的传闻不假。
翰林院的朱长春,身材虽肥胖了一些,但老天爷给朱长春打开了另外一扇窗朱长春的五官长的比较立体,算是胖子中的一枝独秀吧,难怪能在诸多进士中鹤立鸡群。
因为朱长春,他对官场上的一些小癖好有了点认识。……
因为朱长春,他对官场上的一些小癖好有了点认识。
可看到袁珮后,他傻眼了。
袁珮外貌不文雅,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这便也罢了,最主要是独臂啊
漕运总督每年要节制三洲五城的漕粮,还要盘查上万艘船支的官兵以及老百姓,除此之外,南来北往的货商在码头交易时,漕运总督要派人稽查,襄办商税。
总之繁杂的事务需要漕运总督时常在外边抛头露面,可以说漕运总督在一定程度上相当于南北水运的脸面人物,他想不通颜狗十级的敬元帝怎么会派一个杨过把持漕运。
居三四处打听都没带回有关这方面的确切消息,谢行俭觉得打听不到实属正常,毕竟袁珮是淮安城的大佬头头,谁敢在私底下妄议袁珮的缺陷。
饭桌上酒过三巡后,袁珮领着谢行俭往淮安城最大的护城河上走。
一路走来,望着甲板上威风凛凛的水军齐刷刷的朝袁珮恭敬行礼,谢行俭油然心生崇敬。
独臂又如何,能统领好一方将士,震慑住地方的绅粮大户与水运漕帮就行。
袁珮做事风格和向景截然相反,很果断不拖拉。
点了一支五十人的水军给谢行俭后,袁珮直言不讳的请求“江南府近两年水患多,本官遵从皇上旨意,将江南府上交的漕粮一减再减,降至三成,谁知下半年的秋税,江南府竟然颗粒未交。”
谢行俭认真倾听,并不言语。
袁珮凛然立在甲板上,寒风扫过,突兀的空荡手袖迎风扑腾。
谢行俭侧头瞥了一眼,终究按捺住了好奇心。
袁珮继续道“现如今皇上让谢大人巡查江南府,本官想烦请大人替本官问问江南巡抚崔娄秀崔大人,问他下半年的秋税何时送来。”
上门追账
谢行俭裹紧狐绒氅袍,深吸了好几口初冬的寒气,微抬眼眸直视袁珮,好奇的问“不知崔大人欠漕运多少秋税银钱”
“二万三千两。”袁珮说的很干脆。
谢行俭惊的嘴角抽搐,心道敬元帝让他问候问候崔娄秀,袁珮又让他追讨万两税银,光凭这两件事,他就要将崔娄秀从头到尾得罪的透透彻彻。
一个两个的,干嘛要为难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