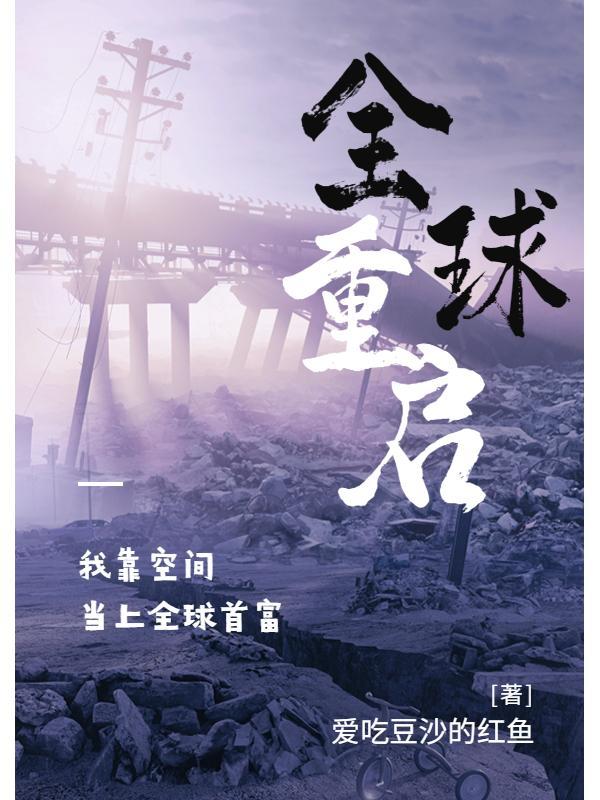看书阁>山野糙汉宠夫记 > 第44章 你有我(第2页)
第44章 你有我(第2页)
白竹经常干活,手上有硬硬的茧子,但小夫郎的手,非常白皙。
现在白皙的手掌根部有好几道血口子,已经开始结痂,唯其黑白分别,更让人觉得格外刺眼睛。
张鸣曦捉着白竹的手,用指头轻轻拂过伤口,突然低下头朝伤口轻轻地呼气:他们从小就这样,只要受伤,就朝伤口吹气,娘说的,呼呼就不疼了!
乡下人经常干活,这些小伤其实可以忽略不计,但张鸣曦觉得这些伤口像是长在自己的心上,疼痛难忍。
望着白竹可怜巴巴的样子,心里的怒火怎么也压抑不住,他冲园子里喊道:“娘,二婶欺负竹子,我去找她算账了!”
白竹刚才哭得眼睛通红,怕被他娘看见,进门的的时候轻轻悄悄的,躲着他们。
他放下背箩,把草药摊开晒了,就去井边洗菌子,没有惊动他们。
胡秋月和宴宴在园子里种菜,一个挖坑,一个撒菜籽,一边干活,一边聊天,根本就不知道白竹回来了。
这时听说白竹被刘杏花欺负,胡秋月一把扛起锄头,几步跨到院子里,紧张地问道:“怎么回事?小竹,她没打你吧?你人没事吧!”
宴宴也小炮弹似的冲过来,拉着白竹的手,一脸焦急。
突然他看见了白竹手上的伤,气愤的喊道:“娘,你看,小哥手破了,出血了!”
胡秋月拉着他的手一看,问道:“你二婶弄的?”
白竹委屈的点点头,还没来得及说话,胡秋月大骂道:“刘杏花这个丧良心的!她竟敢打你!走,我去找她理论去,我的儿夫郎,我家的人,什么时候轮得到她来打?”
她越说越气,重重的“呸”了一声,继续骂道:“这么多年,我不和她计较,忍着她。她爬到我头上,欺负我就算了,还欺负到你头上了!”
说着,一扭头率先出了院子,张鸣曦紧跟着她,边走边把刚才的事告诉了她。
宴宴鬼机灵,锁院门的时候顺手从院墙上扯下了一根细竹棍拿在手上,拉着白竹跟在后面。
胡秋月气愤不已,不住口的低声骂刘杏花。
快到刘杏花院子时,她平息了一下怒气道:“你别冲动,你是小辈,别留口舌给她,让我来问她。”
张鸣曦气昏了头,本想冲上去砸门,听了她娘的话,理智回归了一丢丢,勉强“嗯”了一声。
胡秋月上前拍门:“他二婶,开开门!”
刘杏花正蹲在院子里洗菌子,抢得太多了,半天都洗不完。
她听见只有胡秋月的说话声,心里一松:哼,胡秋月算个屁,她才不怕呢!这么多年胡秋月家的东西她明着要,暗着偷,胡秋月不是不知道,她敢放个屁吗?
白竹这个贱货,还说要告诉张鸣曦,告诉了又怎样?张鸣曦会为他出头吗?会为了他一个丑兮兮的贱哥儿来得罪她这个二婶吗?
哼,胡秋月不提刚才的事就罢了,敢提刚才的事,说出不好听的,她饶不了她!
她站起来,一把拉开院门,气势汹汹的嚷道:“咋了?门都要被你家的人拍坏了!一会儿这个来拍,一会儿那个来拍,烦不烦?拍坏了你得赔!”
说着,一抬头,看见胡秋月和张鸣曦沉着脸并肩站在院门口,宴宴拉着白竹站在后排,白竹眼眶通红,明显哭过。
张鸣曦俊脸乌黑,额头上青筋暴起,一双大眼睛瞪圆了,似乎要喷出火来,将她身上烧个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