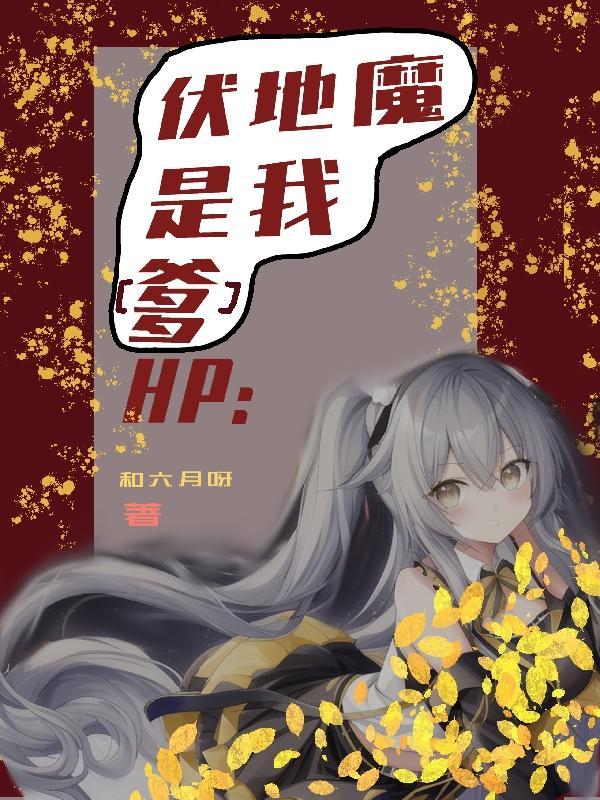看书阁>山野糙汉宠夫记 > 第120章 亲手手(第1页)
第120章 亲手手(第1页)
白竹别过头,心猛的一颤,一股热气直冲气管而来,死命忍住的咳嗽压不住了。
他忙侧过头,对着墙壁猛的咳嗽起来。
张鸣曦心一慌,忙侧过身,一手扶着白竹肩头,一手连连拍着他的背心给他顺气,连声问道:“怎么了?怎么了?怎么突然咳起来了?”
白竹猛咳了一阵,脸都挣红了,额头上青筋暴起,汗都咳出来了,把那口热气咳完,才慢慢停下来。
张鸣曦连连拍着他的后背,给他顺气。
见他慢慢停下来,不咳了,张鸣曦站起来,倒了一碗温水递给他,柔声道:“是不是呛着了?快喝口水顺一顺。”
白竹吓一跳,从来只有夫郎服侍相公的,哪有相公服侍夫郎的?
他受宠若惊,忙伸出双手,想要站起来去接,张鸣曦一只手按在他的肩上,小声道:“不用起来,坐着喝。”
白竹感激地望了他一眼,红着脸,接过碗,顿顿顿地一口气喝了大半碗。
碗里还剩小半碗水,白竹喝不下了,想支起身子站起来,把碗放在灶台上。
张鸣曦的一只手放在他肩上按着他,不让他起来,另一只手接过碗,见碗里还有半碗水,一仰脖子,一口喝完了,抹抹嘴,把碗放在灶台上。
白竹没想到他居然毫不避讳的喝自己的剩水,吃了一惊,瞪大了圆眼睛,着急地道:“怎么喝脏水?你要喝水去倒干净的!”
张鸣曦轻笑一声道:“不脏,我也不渴,喝这一点就够了。”
白竹不知道张鸣曦是什么意思,只觉得他怪怪的,又觉得自己脸上烫,一颗心慌得“咚咚”狂跳,手足无措起来。
他知道的,在乡下,汉子的家庭地位远远高于媳妇和夫郎。
毕竟家里的重活都要靠汉子,外面的大事也需要汉子拿主意。
汉子不高兴了,对屋里的媳妇夫郎想打就打,想骂就骂,媳妇夫郎不敢还手的。
有些汉子会心疼媳妇夫郎,不打不骂,但家庭地位还是一眼就能看出来的。
连晚上洗脚都是汉子先洗了,媳妇夫郎后洗。
只有媳妇夫郎喝汉子的剩水,哪有汉子去喝夫郎的剩水?
白竹脸上烧,身上也热起来了,望着灶里的火,坐立不安,觉得气也不够喘了。
张鸣曦看了他一眼,见他脸红红的,低垂着的睫毛,帘子似的遮着那双水汪汪的大眼睛,正一本正经的盯着灶里的火苗,好像能看出一朵花来。
他心里一动,挨着白竹坐下。
白竹轻轻往里让了让,给他让出一截板凳。
俩人都不说话,彼此之间呼吸可闻,一种暧昧旖旎的感觉轻轻在心头荡漾。
张鸣曦心头微麻,突然觉得嗓子痒,也想咳嗽。
他清咳了一声,侧头看着白竹,见白竹帘子似的睫毛受惊地扑扇着,薄唇紧抿,一副很紧张的样子,突然就很想抱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