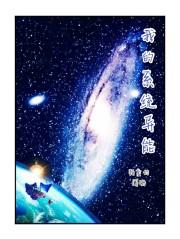看书阁>游行在古代 > 第2章 奇迹附身(第1页)
第2章 奇迹附身(第1页)
天空白云飘飘,山涧流水咚咚。鸟鸣啁啾,悦耳心舒。
一阵刺痛把赤古疼醒,迷迷糊糊,睁开眼睛向四周瞅了一圈。现自己附在一棵树杈上,此时的形状,就像猎人吊在猎枪上四肢软垂的死兔。
挣扎着想翻个身,“叭哒”一声,从三、四米高的树枝上掉到地上。死了,死了,此时不死更待何时?软绵绵躺在地上,四肢无力,犹感觉眼珠还可缓缓旋转。一度想昏迷过去。
脑子里面也没想此刻身在何处,想的是茂中、强仔不知是否在旁侧?仰躺着,努力想侧翻个身却软软的毫无力气。罢了,先躺会儿吧。
天渐渐黑了下来,算了,先睡觉,明天恢复了些力气再计较。
正迷迷糊糊欲睡之时,突然感觉身上似有物爬行,睁眼借着微光一看,顿时寒毛炸竖,惊诧的不自禁张口欲喊。一条犹似小儿臂粗的蜈蚣在赤古的肚腹间游走。
死了,死了,此时不死又待何时?赤古感觉自己不出声音,想把嘴合上却再也无法关闭。就这样像面瘫患者张口嗷嗷待哺,颤栗栗腿间一股暖液流出。
蜈蚣爬到赤古唇边,一头扎进赤古的喉咙,像破处一样硬往里挤。赤古感觉喉间痒痒的,口腔里痛痛的,怕是被蜈蚣硬挤造成的后果。死就死吧,正好肚饿,怎也做个美美的饱死鬼。
约一小时后,腹部传来阵阵绞痛,痛得似临产的孕妇呼天怆地。同时丹田处一股火烧火燎的热气如三昧真火焚烧全身,在全身百脉乱窜,四肢,头顶,脚底,处处炙烤,关节骨骼咔咔作响,这种又痛又火炙的感觉无法言语描述,孙悟空在太上老君丹妒中也不过而此吧!
痛,持续了一夜,汗,洒了一瓢又一瓢。晨光初露,痛疼渐渐平息。
赤古试着坐了起来,记得跳崖时,右手挽着茂中,左手挽着陈强,如果不出所料,他俩定散落在一左一右。因疼痛挣扎了一夜,已经分不清坠落时的定位谁在左谁在右了。
管它呢,先找齐了再说。哪怕是尸体,也必须找到。一想到尸体,一大波寒意浸满全身。
先向左边走去,约二十多来外,只见刘茂中呆呆的坐在草地上。
“你能站起来吗?”赤古问道。刘茂中像傻子一样不言不动。
赤古伸出右手一把拎住他的衣领,往背上一背,往右边走去。约行五十米外,陈强如出一辙似刘茂中呆呆的坐在地上。摔傻了?不死就该庆幸,什么呆?
赤古左手拎住陈强,感觉两个人都轻飘飘的,似乎加起来不足3o斤。饿瘦了?饿瘦了好,以后省米俭布。
把他们放在自己摔落的地方,拍拍俩人的脸颊。
“喂,醒醒,你们的女朋友找你了。”
就见刘茂中,陈强转动着眼珠。
“完了,完了。”刘茂中说。
“坏了,坏了。”陈强喃喃。
“什么完了?坏了?”
“我吃了一个蝎子,完了。”刘茂中道。
“我吞了一只蛤蟆,坏了。”陈强道。
“嗤,以为什么太不了的事。我咽了一条蜈蚣,跟我比,你们真的是小巫见大巫。”赤古向河边走去,口渴,懒得理他们。
他们跟在后面。
“你不担心?”刘茂中追上来问。
“担心什么?”
“担心后遗症呀,毒身亡啊。”
“嗤,要毒早毒了,现在多活一刻我们就多赚一刻,担心个鸟,开开心心过一天是一天。你摔下来没摔断骨头吗?现在不是好利索了?看你活蹦乱跳跟上来的步子,你不觉得这是奇迹?”赤古宽慰道。
刘茂中低头想想是这么个道理。
“蜈蚣也就手指尾或拇指般大,怎么我吞的蛤蟆就比你的蜈蚣小巫见大巫了?”陈强趋上来不甘心蜈蚣比蛤蟆大。
“我咽下的蜈蚣有小儿手臂粗细,明白了没?”
“是不是大浮夸了,这么大你咽得下?”
“信不信由你,是它霸王硬上弓的,不是我自愿的。懂不懂?”
“哦……”陈强半信半疑无言以对。
三人来到河边,捧水掬喝。商议何去何从。爬上这万仞深渊的峭壁是无力为之的,只能绕路而上,或绕路出了这谷底再计议。
收掇了一下丝丝缕缕破烂的衣服,洗了把脸。辨明方向,往南走去,南边是南京城,如果日本鬼子走了,就可以在城周围顺便找些食物填填肚子。
一直走了三天,粗略计算了下路程,翻山越涧,拨草折荆,每天也可徒行4o至5o里。印象中跳崖山顶上直线离南京城也约莫十公里左右,怎么个走了三天还未到?莫非走错了方向?可再次辨别方向,是往南没有错呀!
三人停在一个山巅上,取出河里捕获已经烤熟的鱼干,边吃边商量。下了此山,是一望无际碧绿的草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