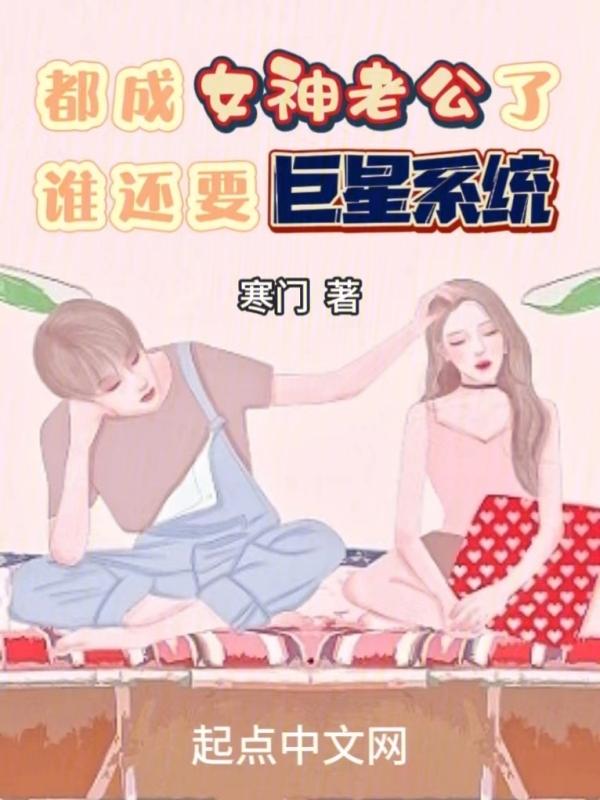看书阁>凤鸾华章 > 第五十章 存余悸妙弋避走北平(第1页)
第五十章 存余悸妙弋避走北平(第1页)
驸马的眼神呆滞,状如痴儿,他遗忘了前事,无牵无挂,无忧无虑。在宝硕的悉心照料下,他逐渐对她依赖起来,渴了同她要水喝,饿了缠着她喂饭吃,她总会及时地满足他,像对待一个她深爱的孩子。
朱棣践行着他的诺言,每隔五日,都会在6羽茶楼,那个相同的位置,告知妙弋驸马的近况。可两个五日过去了,却依旧没有等来柳岸痊愈的消息。
她失望已极,沮丧地对朱棣道“看来是没什么希望了,柳岸此生完了,宝硕不会甘心长久地陪伴一个长不大的孩子……是我害了他们……”
朱棣却道“不,相反,我见宝硕很有一股韧劲儿,她坚信驸马一定可以记起她,爱上她。”
妙弋认定是自己连累了宝硕和柳岸,因引咎自责,她心神不定,整日郁郁寡欢。离了茶楼,才回府邸,她便接到从北平府来的信函,看字迹,不是常茂还能是谁。
她立在小轩窗旁,一目十行地读完了信上的内容,与往常一样,不过是些对军旅生活的体悟,对家乡和故人的思念……她自言自语道“还是你过的洒脱自在,应天城总有许多躲不开的尔虞我诈,是是非非。”
她将信笺收纳在多宝格上一只小方匣内,里面尽是常茂从戎后给她的来信,满满当当的,需得往下压一压才合得上了。
盈月掀帘入内道“小姐,夫人刚从宫里回来,您今日还未曾问安,现在要过去吗?”
妙弋点头,盈月跟随着她走出一重院落,拐进另一进庭院。小弟小妹正在院中游廊上追逐嬉戏,见长姐来了,都伸着手臂朝她跑来,她蹲下身,唤着“膺绪,夙伊,你们想姐姐了么?”
“想姐姐……姐姐带我去骑大马。”两个小娃娃犹记得被长姐带去马房试骑风神翼时的欢欣鼓舞。
妙弋道“你们乖乖听话,姐姐不但带你们去骑大马,将来还要教你们打马球呢。”
与他们玩逗了会儿,她才抱起小妹,牵着小弟向房内行去。刚走到窗下,忽听母亲与近侍嬷嬷闲话道“陛下和娘娘之意,近日怕是要为妙弋指婚了,可皇子们将来都是要去各自的藩地的,一想到妙弋要离开应天,离开我,我这心里就难受得紧。”
她的心骤然揪紧,连步子都迈不动了。只听嬷嬷问道“尚未立过正妃,又比小姐年长的皇子,有晋王,燕王和周王,夫人之见,陛下和娘娘会将小姐指给哪位殿下呢?”
谢夫人道“若按照长幼次序,晋王的可能性更大。。。。。。”
妙弋猝不及防,心中的难过之感莫可名状,她放下怀中的小妹,转身将小弟小妹的手交到盈月手中,只对她说了句“替我送他们回去”,便头也不回地跑走了。
她有种被遗弃了的感觉,虽知身为女子始终会有这么一天,却不曾预料会来的如此突然。嫁给晋王?她苦笑连连,那个还未选立正妃便已迫不及待地接连纳娶妾室的浪荡王爷。。。。。。她犹记得,晋王与侧妃画苒在公主府时频频为难她和柳岸。他行事随性而为,不计后果,对妾室娇宠无度,且看画苒待人接物时的浮浪不经便可知一二,她是无论如何不愿委身晋王的。
突然,妙弋冒出一个大胆的念头。回到房中,她重新取出常茂的信笺,反复看着信中的那一句,‘一月后大军将会开拔深入漠北腹地进剿鞑靼。’
推算过日期,这封信从北平府寄送到她手中耗时十日,她完全有机会在大军开拔前亲赴北平见到常茂,不过,须得提前知会他做好接应。她走到书案后,开始给他回信,想着驿使若能在十日左右将回信交到他的手中,她便有望混入军中,与大军一同开拔。她迫切想要逃离应天,如今多呆一日都觉是种负累。
写罢回信,再以火漆封缄。妙弋又铺开素笺,这一封则是留给母亲的。。。。。。
放下毛笔,她起身正要离开书案,忽觉脚下绊到何物,低头察看时,却是前几日朱棣拿去茶楼送予她的礼盒。连日来为柳岸与宝硕之事担忧,叫盈月放在此处后竟一直忘了拆看。她将这件份量颇重的礼盒搬至书案上,解开绳结,掀去盒盖,往内看时,只觉一阵感动,继而鼻酸眼热起来。
那是一尊烧造的栩栩如生,与风神翼一般无二的神骏,朱棣命人将它还原的何其逼真,瓷马通体乌黑亮,四蹄踏雪,就连鞍披上的纹饰都与风神翼从前所佩戴过的如出一辙。她半抱住案上的瓷马,将脸颊贴在冰凉莹润的釉面上,幽幽地道“风神翼,你若还在,便能随我一起去北平府,去漠北了。。。。。。”
一位头戴遮日黑箬笠,白衣佩剑,身骑银鬃黄骠马的少年在官道上一路驰奔,与巍峨矗立的应天城楼渐行渐远。
谢夫人现妙弋离家出走时已是一日之后,她心急火燎地盘问着盈月,直到口干舌燥也未问出个所以然来。盈月跪在夫人膝前,抱着她的腿,哭的情真意切,连她自己都开始相信小姐出走之事她并不知情了。
嬷嬷们很快从小姐卧房的琴桌上现了一封书信,呈给夫人看过,她垂下拿着信的手,伤怀道“应天府怎么就让你觉得压抑到喘不过气了?你说要出去散散心,可你到底去了哪里……”
允恭闻讯赶来,从母亲手中接过信笺看了,安慰她道“娘,看来长姐是早有预谋的,以她的武功和才智在江湖上闯荡必定不会吃亏,您也别太过忧心。”
盈月抽泣着附和道“正是,我见小姐带走的皆是男装,想来她是做过一番乔装改扮的。夫人,如果小姐只是想出去散心的话,不妨就让她去吧,这些日子,因宝硕公主和驸马的事,小姐茶饭不香,人都清减了许多。”
谢夫人支着头,惆怅满怀,她语重心长地对盈月道“小姐决定出走前一定会留下些蛛丝马迹的,你是她最信任和倚重的侍婢,却说不曾有过分毫的觉察,我可不信!你要听小姐的话,替她守口如瓶,实则是在害她。”
盈月默想着,定得替小姐坚守住秘密,她才离开一天,离北平府还远着呢,若被夫人知道了,必会派人去追,小姐的计划可就功亏一篑了。
夫人见盈月眼珠骨碌碌地打转,却缄口不言,分明在刻意隐瞒什么,她朝允恭些微暗示了下,允恭即刻会意,将盈月从地上搀扶起,道“我相信盈月不会欺骗娘,您就别再为难她了,”又对她道“你回房去吧,要再想起与小姐行迹有关的事,就快来通报给我。”
盈月长舒一口气,逃也似地离开了夫人的视线,却在走进自己房门前又被允恭给叫住了。她返身无奈地道“允恭少爷,你不是说相信我么,怎么还不放过我?”
允恭坏笑着道“我那是在夫人面前替你解围,现在轮到你来回报我了,说吧,我长姐去了哪儿?你放心,我不会告诉夫人,只想确定长姐栖身之处是否安全。”
盈月想,允恭定是来诈她的,他若知道了,夫人那儿恐怕也瞒不住,便道“我猜,小姐可能回濠州去了吧,允恭少爷,你说故乡的老宅那儿安全吗?”
允恭打着哈哈,以为套出了实话。谢夫人很快也便知道了,她当即抽调府兵,命他们星夜往濠州方向追赶,不可疏漏沿途官道上任何一间客栈。
派遣停当,她叹息着对允恭道“难道真是我平日里太过宽纵你姐姐了,可她一向谨慎持重,循途守辙,从不会做出逾矩之事,她到底是为了什么。。。。。。”
允恭端了杯热茶呈给母亲,道“娘,等追回长姐,我再替您好好审她,您喝口茶顺顺气儿,可别急坏了身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