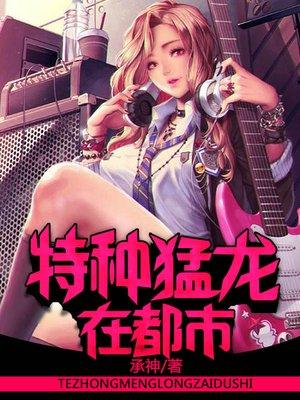看书阁>折刃 > 第52章(第1页)
第52章(第1页)
他羞恼的站起来,面对对方质疑的目光,咳嗽了一声:“我剪一下灯芯。”
“剪什么灯芯?”福嘉按住他,下巴轻抬,直接吹熄了烛火。
两个人的呼吸声,在黑暗中显得格外沉。福嘉压着他衣摆的手没有松开:“在行宫那晚,我亲过你,还记得吗?”
兰烽心如擂鼓,可是同样的问题,问一遍就够了,他不想再重复了,只能冷硬地挤出几个字:“是臣唐突了殿下。”
福嘉继续柔声道:“我昨晚听田娘子说起,才知道一件事,你猜猜,是什么事?”
兰烽没说话,方才的一腔燥热慢慢凉下来。她是来质问他的。
“昨天早上,”他平静看着她身旁:“我们在庆州城门附近遇到曹暄鹤了,我让你们等一下,是想等他走了再进去。”
“啊,”福嘉表现的很意外:“还有这种事?但我要说的不是这个。”
她好像对那件事并不感兴趣,自问自答道:“我要说的是,我一直以为中了鸳鸯蛊,二人皆会被蛊虫驱策,只是中母蛊之人症状会轻一些——毕竟你当时是这样的。但是田娘子却告诉我,母蛊并没有任何症状……”
福嘉指尖握紧他的衣摆,她心跳的很快,声音也有些发颤:“兰烽,可我却觉得你当时也很……难受。你能告诉我,是为什么吗?”
成功听到对方紊乱的呼吸声,她的手向上摸索,刚好碰到他的膝盖。
她收紧手指,听到对方浑身僵硬地重复道:“是臣唐突……”
没问出想要的答案,福嘉的手是温软的,嘴上却咄咄逼人:“哦,这样啊。那我还有一个问题,你在城门外拦着我,先让曹暄鹤走,又是为什么?”
眼睛适应了昏暗的光线,她看见兰烽慢慢转过脸来,眸子渐渐灰败暗淡下去,他咬牙答道:“对不起,我鬼迷心窍,怕你和曹暄鹤见面旧情复燃。”
“好奇怪,”福嘉不打算放过她,她脸颊烧得滚烫,凑近了问:“我和曹暄鹤旧情复燃,你为什么鬼迷心窍?”
见兰烽身子晃了一下,她心一横。干脆鼓起勇气,摸索着向上,她的指尖划过少年的肩膀和脖子,最终,捧起他的脸。她想让他与自己对视,澄澈的目光落进他眼中。
“我和曹暄鹤见面,你心里难受,是因为吃醋。明明中的是母蛊,却会动情,是因为抱着的人是我。”她说:“兰烽,你现在是不是喜欢我?”
客栈外,水川县的夜市很热闹,听说有酒楼瓦子,夜烛能燃至三更天。
喧闹声时而很近,又仿佛很远。
福嘉看着他的神色有片刻诧异,他们相隔咫尺,呼吸近乎交织,他身上干净冷清的像带着雪的气味。
她听见兰烽咬了咬牙,一字一顿地:“我是。”
福嘉忍不住笑了。
那笑带着点戏谑,她很快遭遇误解,兰烽别过眼:“别笑。”
“不是笑你。我没去见曹暄鹤,”她停顿片刻:“因为想来见你。”
兰烽冷冷看着她,她凑上自己柔软的唇:“现在没有中鸳鸯蛊,你不算趁人之危。”
他眸光滚烫:“你知道你在做什么吗?”
福嘉垂下眼,手轻轻搭在他肩上:“嗯。”
兰烽没有再说什么多余的话,翻身将她压在榻上。
“你说过,我们是夫妻。”他呼吸炽热,却没有立刻去碰她。
“合法夫妻,御赐良缘,三书六礼,门当户对,”福嘉一双眼温顺如水:“你是我主动求来的驸马。”
黑暗中有裂帛声响,清冷的气息覆上来,福嘉对上秀丽的眉眼,却看到里面混杂着她从未见过的欲念与疯癫。眸光如火,烧得她浑身滚烫,她到底是有些害怕的,却依然生涩而乖巧地努力回应他。
三更天后,打更声歇,城内喧闹渐停。纵然福嘉傍晚吃了茶,这时候也有些受不住,她小声央求,兰烽却没饶过她,他耐心哄了会儿,只让她听话。
第二天他是神清气爽的起来了,福嘉一觉睡到晌午过后才迷迷瞪瞪有了动静。她赤足踩着绣鞋要下床,兰烽赶紧上前抱住她。
她拢好衣衫,也确实拉不下脸叫外头不够贴身的随侍伺候。兰烽倒是也顾忌她了,脖子手指,他都没动,其他地方却实在有些惨不忍睹,浑身像被碾过。
兰烽试了试水温:“先沐浴吗?”
福嘉点点头,余光看见他左手食指上的血痕,是她昨晚咬的。
他手掌大,指尖全是茧子,搅在她嘴里像砂纸。她心里暗道活该,耳根发红的把自己沉进水里。
趁着福嘉沐浴,兰烽去厨房把炖了几个时辰的驼蹄羹盛出来,又换了个好看的青岫瓷盅,楚蕈和笋干鲜嫩爽口,佐以葱姜胡椒,汁浓如乳,清香扑鼻。
福嘉匆匆洗漱完便问道香味,顿时食指大动。
兰烽在旁陪着她,她小口小口,安静地把整盅吃完,显然是饿了。
回程时间不紧,两人共乘一骑,兰烽一直将她箍在怀里,温热的呼吸都扑在她后颈。他还是冷淡中有些漠然的性子,福嘉却说不上有哪里不一样了。
她晕乎乎思索了一路,想出一点不同来。兰烽原先避讳同他亲近,如今有了几分强硬,好像真的把她当做自己的所有物。
福嘉有些头疼,她本意不是如此。
不过看得出他在兴头上,也就先由着他几日吧。
兰烽把福嘉带回庆州内城安置好,便开始忙起来了,一连几日都是深夜才回来。
有一天福嘉睡着了,感觉一个凉嗖嗖的怀抱从背后包裹住她。
她还不习惯同一个男子耳鬓厮磨,睡梦中挣了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