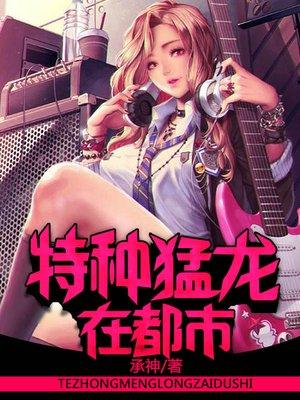看书阁>折刃 > 第80章(第1页)
第80章(第1页)
兰烽这样的人,恐怕除了福嘉,没碰过别的小娘子,既不懂女人心思,也无力消化福嘉与其他男人之前的牵扯。
这时候,其实只要兰烽服软示弱,福嘉性子惰,是狠不下心来主动同他分开的。可兰烽是个毛头小子,稍有刺激便会偏执的地钻牛角尖。
反倒给了他大把趁虚而入的机会。
他甚至不用做什么,只要顺应天时,以公事之便,同福嘉私下多见几次,这位小郎君便会自乱阵脚,亲手毁了同福嘉仅剩的一点情分。
一场戏落幕,胡姬顶着严寒,穿着单薄的衣裙出来跳胡旋舞,福嘉有些乏了,曹暄鹤便体贴道:“臣送殿下回去吧。”
福嘉点头,披着狐裘拨开纱帘。外面很吵,她皱起眉头。
曹暄鹤眸子微动,对福嘉道:“方才走的那条路有些拥挤,不如从后面的小路走。”
福嘉不疑有他,跟着曹暄鹤绕到戏棚后,穿过两道月亮门,总算安静下来。
寒风袭来,她打了个哆嗦,曹暄鹤犹豫了一下,还是替她拢了拢衣带:“当心着凉。”
福嘉的手其实从里面正捏着领口的绒花,曹暄鹤的手指伸过来,刚巧碰上她的。
福嘉正走神,被碰到时下意识缩了一下,曹暄鹤不着痕迹的松开手,却没再继续保持之前的距离,与她挨得很近。
前面是条窄窄的石桥,水面上结着冰,曹暄鹤自己上了桥,便回身来虚扶着福嘉:“殿下小心。”
这次福嘉没拒绝,顺着他的动作往上走。
两人还没完全走上桥,曹暄鹤那只手忽然被人从背后扭住。
他回过头,见兰烽不知何时来的,双目发红,手里还抱着个包裹。
被他看着,兰烽松开手:“别碰她。”
曹暄鹤丝毫不怒,只是疑惑,随福嘉一起来的,随他一起来的,合计里里外外得有十几二十号随从,他怎么进来的?
他动了动手腕,微微笑着道:“哟,这不是兰驸马吗?我还说,是哪里多出个小尾巴。”
兰烽脸色铁青,刚要张口,却听见福嘉站在两人侧边,轻声道:“暄鹤,他已经不是驸马了,你该改口叫兰四厢。”
兰烽梗着脊背,话到嘴边,顿时忘了干净,脑中只剩下那句“他已经不是驸马了”。
几个时辰前,白禾劝她早些告诉他真相,她明明还在犹豫。
十几个时辰前,他奔波数日,心里想着她见到他时的惊喜,再多劳苦都甘之如饴。
不过短短一夜,他再站在她面前,拦着别的男人碰她,她就撇清同他的关系了。
兰烽终究是转不过这个弯,怎么能这样快,他还来不及反应,她就变了卦?
想到昨日他赌气说的那句话,兰烽心脏颤痛,他怎么就能把那样的话随口说出来。福嘉一定伤心至极,恨透了他。
曹暄鹤玩味的观察两人神色,知道点到为止的道理。
他颇有风度地拱手道:“殿下想必还有些私事,臣不便叨扰,这就先回去了。”
福嘉让随从在外守着,冲曹暄鹤“嗯”了声:“多谢。”
他一走,兰烽立刻低下头,看着福嘉,他眼尾发红,语气有些乱:“墨尔,对不起。我昨晚说的是气话……我从来没喜欢过别人,也不在乎能不能封王拜相……”
他打好腹稿的那些话,全都散了,他尽力把他们拢起来,送到她面前:“你如果担心边防,孔五郎若是不愿意留在环州,我这里还可以举荐薛虞候……”
“兰烽,”福嘉打断了她,她仰着脸看他,透亮的眸子里无喜无悲,带着柔和的光泽:“你先听我说。”
那神色让兰烽心头一紧:“好,你先说。”
福嘉指着他手里的包裹:“这是给我的吗?”
兰烽点点头,看着她发顶璀璨的金钗,又觉得拿不出手。
福嘉自己接过去,打开:“很好看。”
她把金钗取下来,换了玉钗,又带上玉镯,还把雪白的手腕抬起来晃晃:“你的东西我收下了,也接受你的道歉,你不必为昨天的事愧疚了。”
兰烽心底全是恐慌,他喉咙苦涩,艰难开口:“不是,墨尔。”
福嘉笑一笑:“兰烽,这些话,我一直想告诉你,但我也是个懦弱的人,找不到开口的机会,让我一次说完,不要打断我,好不好。”
兰烽浑身发抖,咬牙摇着头,却果真没开口打断她。
福嘉替他理了理衣襟:“你现在功不配位,朝中多有非议,说我耽误你前程,说果然有志儿郎不能尚主。的确,你手握重兵,却碍于驸马的身份,再难封赏。”
她垂下手,慢慢转过身子,背对着他继续道:“我昨晚一直想了一夜,长痛不如短痛,我们还是分开吧。你放心,一定不会亏待你,宗正寺的碟文出来,陛下就会下旨封你做环州知州,兼任环庆经略史,你现在边关委屈几年,等立了功,就调你回枢密院做副使。现在的枢密使年纪大,也没什么根基,你好好干,三十岁便能坐上曹枢使的位置。”
兰烽听的目眦尽裂,他终于忍不住,捏着福嘉的肩膀,让她同自己对视:“李墨尔,你看着我!”
对上她澄澈的眼,他忽然委屈起来:“你当真……不要我了吗?”
福嘉任他巨大的阴影笼罩在身上,轻轻地说:“是啊,不过我们之间,从一开始,成亲的那夜,不就说好了,会在这一天分开吗?”
她看着他:“我的心上人回来了,我不能再留你。”
闻言
知道是一码事,听福嘉亲口说出来又是另外一码事。几乎是一瞬间,兰烽黑白分明的瞳孔里就拧出狰狞的血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