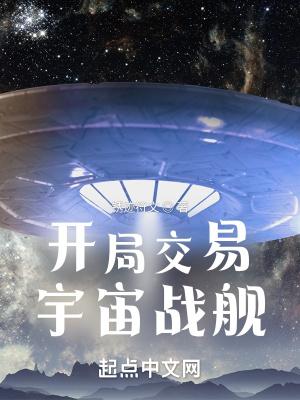看书阁>太子何故变gay子?[穿越] > 第85章(第1页)
第85章(第1页)
他已经分不清,自己是在救援直升机上,还是在冰冷的潭水里了。
“怎么会染了疫病”皇帝站起来,在殿前走来走去,心情越来越焦躁,“朕去瞧瞧贵妃。”
“陛下,陛下!不能去呀陛下,臣等尚未查明疫病来源,只怕会传染。听说城里也有少数百姓也出现了类似症状,颈部背部都有枝茎似的黑色脉络,极其可怕。”
“宣翼王进京,就说他母亲病重,速来。”皇帝扭头对宦官吩咐道,“朕要拟旨,拿笔来。”
他一气呵成写完了一道圣旨,准备摁章,却突然有些不忍下手,犹豫再三,他拿起玉玺。
有人扣住他的手腕,叹了一声。
“父亲。”
皇帝愤怒地扭头,看见一双哀伤的眼睛。
“有人算出你生了异心,现在看来没算错。”他缓缓说道,“你竟为了一个沈瑛要杀你君主、你的父亲不成”
“父亲错了,异心是算不出来的。”李习璟扣了扣桌案,一个人端着托盘,从门口疾步而来,跪于二人面前,李习璟继续说道,“儿子是为了江山而来。”
皇帝看着眼前的灵虚子将一碗汤药置放在自己面前,终于笑出来声,“哈哈哈,璟儿啊璟儿,你可真是朕的好儿子,朕以为你是临时起意背水一搏,不料原来布局已久么。”
“是,即便父亲当时没有临途易辙,儿子自然安排了其他道长在别处等您,”那壶里有毕诺给的方子所以才有立竿见影的疗效,因为怕被闻出来,灵虚子不敢多放,好在见效很快,也因此取得皇帝的信任…太子端起面前那一碗汤药,“父亲的亲卫已被支开了,至于支不开的……”
梁上滚落颗人头是答案。随后几个人影跳下来,将带下来的身体一起堆在一旁。
“父亲,儿子不忍看百姓受难,亦不忍见父亲为病疼所害,这碗药是儿子为父亲准备的生辰礼,想来也到不了那天,父亲今日就将儿子的心意喝下吧。”
那本是皇帝最熟悉的药味,此刻令他猛烈地咳了起来,他说:“你想当皇帝,朕会让位给你。”
“你从小就是朕最喜欢的孩子,知书达礼,颇有尧舜之资,今要杀父岂非糊涂?”皇帝问。
&ot;父亲是错信妖道、误饮奇毒而亡,非儿臣手刃。岂有弑父之说?父皇频频瞥向门口,可是盼新太子来救?可惜没有新太子,倒是将有新皇。此刻宫外已为我军所围,三哥亦在途中被我截获。&ot;李习璟紧握皇帝后颈,药碗递至唇边,冷声道:&ot;父亲何必拖延时间,去得不干脆。&ot;
皇帝攥着拳道:“你弑君弑父争权夺位,此等逆天悖理之行,必然受千古唾骂!”
李习璟只是微微笑着。
那日灵虚子对他进言,他已心生疑窦,暗中调遣重兵,固守京畿,以防万一。不料李习璟敢在这时带亲兵逼宫。
皇帝见事已至此,无可挽回,遂饮下那碗汤药,继而愤然摔碗。余下的药汁飞溅,沾染李习璟衣袂,他却毫不在意,静观帝气绝而亡。
居然是这么轻易的一件事。他想。
他和谋士们商量出了各种可能,甚至连失败后的情况也考虑了。没想到会这样轻易骗过他当了几十年皇帝的父亲。
他并未率兵围宫,亦没遣人阻截李习越——精锐尽在此殿,且能潜入已属不易,何敢奢望更多。
太轻易了,以至于让他怀疑,皇帝是不是真的死了。他探了探鼻息,随后他落了泪。
这场篡弑匆忙而就,漏洞百出,然他一一镇压异声,有谁敢对先帝之死提出异议,便斩立决,直至满朝无人再敢言及此事。
李习璟高坐龙椅,百官跪地臣服。他的王途染满了鲜血,他是踏着还冒着血气的尸骨爬上这个位置的。
皇帝死后,他本想将李习越一块儿杀了。不料听说李习越也染了和贵妃一样的传染病,一病不起。他便假装好弟弟去探望李习越。
李习越已经病得下不了床。李习璟却没有体恤他的打算。
他说:“三哥病重,太医说根在双腿,唯有摘去双腿方有一线生机……飞枚。”
李习越看见一个蒙着口鼻的男人握着锯子掀开薄纱,到了他床榻边。
他笑得像要断气一样,“皇帝死了,你就要拿我开刀给沈瑛报仇啦?哈哈哈,你现在就是把我锯成肉沫,他能复活么?李习璟,我觉得你真可怜。从前你还称得上伪君子,如今连君子也不装了,只当疯子。”
李习璟充耳不闻,道:“动手。”
李习越还在骂李习璟,等飞枚将钝得生锈的锯子嵌入他的肉里,他再也发不出除惨叫以外的声音。
没一会儿,他疼晕了过去。再醒来时只感觉大腿下空荡荡的,脸异常火辣。有人在不留余力地扇着他,见他睁眼,这才停下。
“本想杀你,但仔细想想那对你来说太轻松,”李习璟的声音从不远处传来,“你死前多些痛苦孤才高兴。可惜这病来势汹汹,恐怕你等不到大典就死去了。”
李习越只是一动不动地眨眼。
这病只感染这些不属于这里的人,毕诺也染病了,他说他大概要回家了。
李习璟已猜到沈瑛跳进了那口奇潭,他问毕诺:“你回去后能找到他吗?”
毕诺思考了一下,回答:“不太好找,殿下,你不知道我们那儿有多大,又有多少人,虽然有互联网,但是找一个完全没有联系的人也是有点难的。”
太子:“如果你能找到他,你帮孤跟他说……”
毕诺等了半天,没有等到下文,“殿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