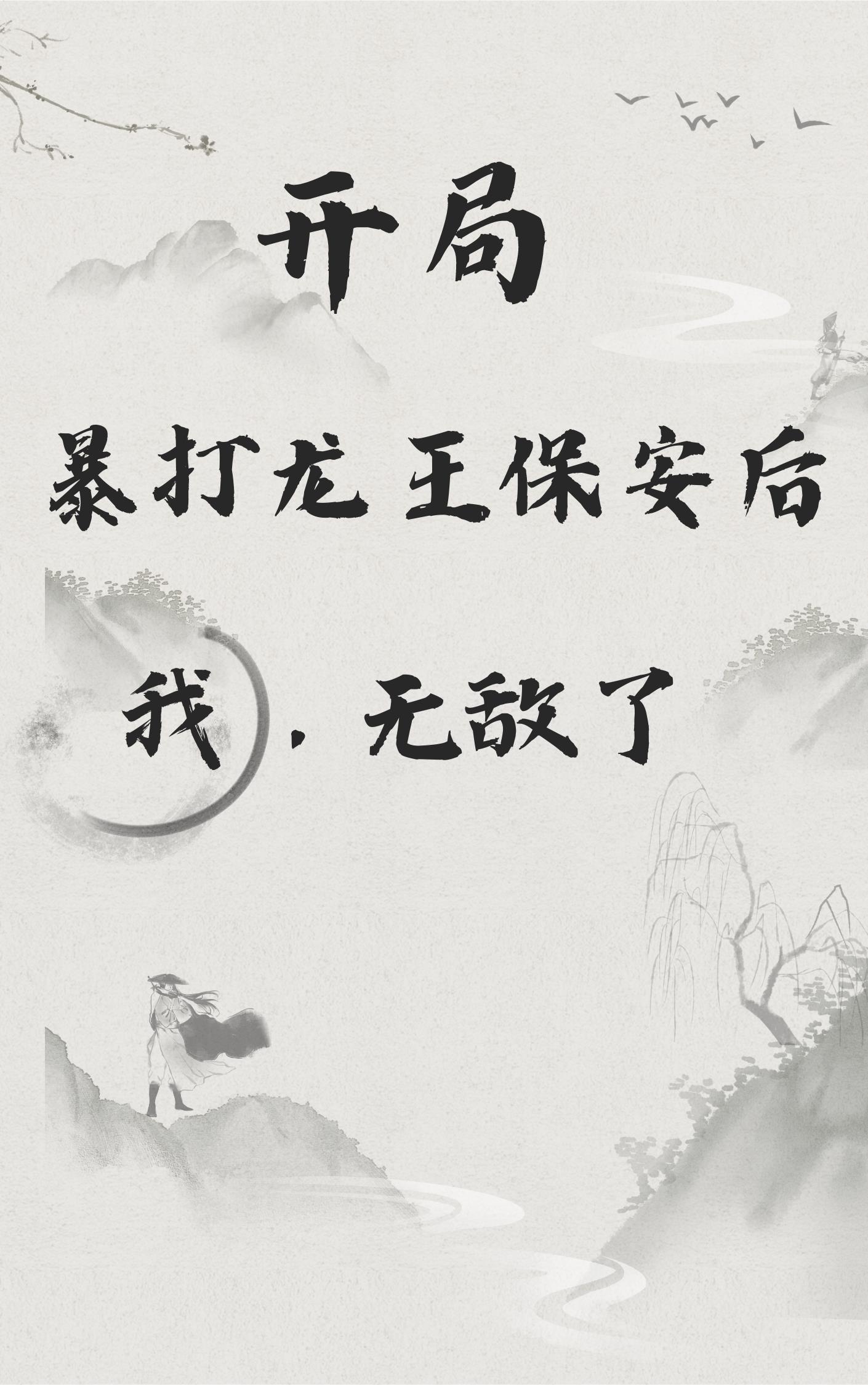看书阁>春惊寒食 > 第一百六十九章 命运循环重要(第2页)
第一百六十九章 命运循环重要(第2页)
你就这么见不得我好,我好不容易嫁出去,你就非得这么地使绊子、给我难堪?
我承认我做的事情并不光彩,也不体面,可日子总得过下去,你到底为什么来?”
沈自丹突然失控,疯狂暴怒,一掌击开挡在前面的顾沉星,闪现一般突然出现在戈舒夜的面前,双手扼住戈舒夜的双臂,指甲几乎要陷入她的血肉,他咬牙切齿地道:“戈舒夜,你想离开就离开,你想嫁人就嫁人吗?你生是西厂的人,死是西厂的鬼!”
戈舒夜难以理解沈自丹,道:“可我已经有孩子了。”
“把孩子生下来,我来做她的爹爹。”
云头堡的众人都站起来,不安地围着他们。
戈舒夜突然抬头看着沈自丹的脸,由于春水灵力的存在,他的面容和她第一次见到他时没有什么区别,他还是那个被命运之神捉弄,却仍被水神偏爱的水神之子——他清隽的面容,他美丽的眼睛,就像他第一次映入她的眼帘,拨动她年轻的心弦。
人年少,则慕父母;及长,知好色而慕少艾。
(人年幼的时候,依恋自己的父母;等到年岁渐长、春心萌动,产生了爱美之心,就会爱慕年轻美丽的异性)
那是她第一次凭借自己的眼睛和自己的心爱慕上的少年啊,那是她的第一个梦啊。
可是他的眼神疯狂,像是被什么催动。
可是她却在时间中流浪了十年,她的时间前进了,她不再是那个天真、没精打采的少女,她是一个时间中的女人了。
第一次,她比他更敏锐,比他更聪明了。
她抬起手来,摸了摸他的脸:“沈芸,说你真正要说的话。”
沈自丹透明的眼睛中流露出天真的、近乎疯狂的渴望的光,摸了摸戈舒夜覆在他脸颊上的手:
“我找到药师之血复原身体的方法了,我可以娶你了。”
戈舒夜感到自己的心脏像是被一只巨大的手攥住,像是拧毛巾似的用力挤压,仿佛所有的血液和力气都被从心脏中挤走了。
她抱着自己的双臂,几乎要站不住,脱力地蹲下去了。
从十七岁开始,她就在等着他的回答,她一直等啊、等啊,等到长城都倒了,等到黄河都干了,等到打败了海盗,等到葡萄牙人到了满剌加。
就好像她是为了等这句话而活着的一样。
就好像这句话将她困在了十年前的黄河边上,她像个孤魂野鬼似的总在原地打转——
十年了,沈芸终于还了她那句回答,她终于自由了。
(戈舒夜执念真重啊,她一直等的就只是一句话。就是在让沈芸承认他喜欢过她,因为她感觉到了。
“未完成情结”重到要死。
值得吗?
但是她就是在等着一句话,不然她的灵魂就被困在原地,没法前进。沈芸说了这句话之后,反而能将她的灵魂从云头堡的原地解放出来,她可以和顾沉星展真实的爱情了。真的执念好重啊,难以形容。
但倒霉的是沈芸又在新的执念里出不来了。
好错位啊!
命运,你就是以万物为刍狗,以玩弄他们的情感为乐!)
她的梦实现了;可是同时,这个犹如七彩肥皂泡一样虚无的梦境,也破碎了。
她一直在追求他的回答,就仿佛他回答了,山海就可以为之移动、天地就可以为之倾覆,时间就可以为此倒流,奇迹就可以为之生似的,就好像世间的一切遗憾就可以补完,世间的一切错误就可以消弭,隔在他们之间的山海、现实、血海深仇和他身躯的不完整、他岌岌可危又炙手可热的政治白手套地位就可以因此改变似的。
他终于承认了。
可是什么都没有改变,她的窘迫、她的难堪,她晦暝不清的前路;他的疯狂,他的贪婪,他不能再抑制的野望;药师依然会被诛杀,海盗依然会来,大明的巨轮依然朝着历史为它铆定的前路而去,地上的人依旧这么冷漠而贪婪。
我为了追求一个梦,失去了一切——可回过头来,什么都没有改变,
连我的车辙,也是这么泥泞而扭曲。
冥冥啊,冥冥,你没有仁慈!
她在原地突然自嘲地笑起来。
沈自丹却陷入了新的执念,他自顾自地道:“真可惜,当年那群人应当一起带走我和小妹的——
他们不知道的秘密,今日被我得知。只有星月药师一起下入血池,白剑开启无厚度之泉,一切才能实现!
这是冥冥对我的祝福,这是冥冥对我的偏爱。
所以,我要带走顾沉星和苏惹月,我要用他们合成的星月药师之血,完成血池之术!”
命运开始重复,故事开始循环,角色开始互换——三十年前因为追杀药师的人而家破人亡的受害者的少年,终于在命运的磋磨下,变成了加害者。在权力欲望的催动下,在恢复身体的愿望的抽打下,在嫉妒和渴望之中,他像那些曾经追逐药师之血的人一样,开始拜服于强权,开始重新向药师举起屠刀。
不行。她心里说;就仿佛她代替三十年前那个站在沈府的戈云止,不,腾骧左卫的云武,说出他本来该说的那句话似的。
他们受困于权力地位、是这个社会关系中的一份子,他们不能反抗权力。
可是我还可以。
我还有我的刀。
“不行。”戈舒夜缓缓地摇头,坚定地说。
“你应当不喜欢苏惹月吧,她死了,你不应该开心吗?”
戈舒夜站起来,心痛让她的每一个字都很艰难,但是她缓慢地将所有的字都说出来,如同吐出一颗颗铅弹:“保护药师是我的职责,你不能伤害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