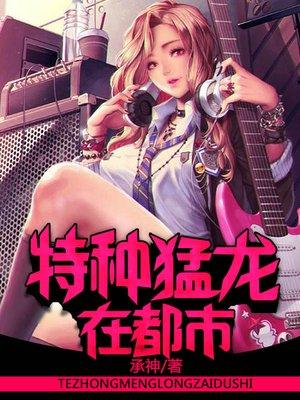看书阁>剑如夕 > 第六十三回 江湖少年(第1页)
第六十三回 江湖少年(第1页)
忽然,门外飞来一剑,“铮”的一声打在顾旸剑柄上,虽力道不大,却也让顾旸手上一抖,那剑便缓了下来。
苏国南吓得后退数步。
顾旸定睛看时,一个武士闯进寨来,提起地上剑,双臂护住苏国南,昂然而立。
此人紫棠色脸颊,耳大须长,正是苏国南部下的将官任行,也是当时在阳谷县跟吴信等三人一起擒住顾旸的武士之一。
任行厉声道:“顾旸,休伤吾主!”
顾旸道:“量你一个人,敌得过我么?”
任行道:“任某未必敌得过你,但平日也算得爱护士卒。倘若你今日杀得我二人离去,手下士卒必舍死相报,恐你难踏出营门半步!”
“说得好!”顾旸大笑收剑,走过任行身边,拍了拍他肩膀道,“你这人行。”
顾旸一面转头怒视苏国南,喝道:“老贼,我今日饶你一命,异日相见,必杀汝以报诸位义和拳领之仇!”
苏国南冷笑道:“你小子出息了!”
顾旸听他仍在有意嘲讽,手中剑颤个不停,但还是忍着怒,把剑一攥,转身出寨。
“顾少侠,且慢!”背后任行叫道。
“怎么?”顾旸回转身来。
任行道:“苏大人所言,乃是哄顾少侠的。赵三多未曾捉住,其余领也未处死,尽都押解上京。”
顾旸听得,眉目间顿现惊喜,但又微皱眉头,道:“所言当真?”
任行道:“当真。”
顾旸抱拳一笑,道:“多谢了。”
话音未落,他忽然又想到阿黎不知在何处,但念及方才直呼苏国南“老贼”“狗官”,却又不好问。
但可以保证的是阿黎在她爹这里,必定安全得很,不如缓图再见。
顾旸想到此刻救援阎书勤等人才是第一大事,便转身提剑而去。
苏国南望着顾旸的背影渐渐消失在营门口,转头瞪着任行道:“谁教你说与这臭小子听的?”
任行笑道:“末将也只是说出大人的心里话罢了。”
“哦?”苏国南哼了一声,脸上却宽和了许多,转身扶着床栏杆,慢慢坐下,“甚么心里话?”
任行道:“末将跟随大人已久,如何不晓得?昨日这顾旸兄弟初来之时,……”
“大胆。”苏国南忽道。
任行慌忙道:“啊……末将忘了大人已与他结为兄弟。昨日这顾大人……昨日这顾少侠初来之时,末将便看到他屡次相望大小姐,模样又熟悉,便猜出几分。大小姐也是心不在焉,想起在阳谷之时,她便似已对这顾少侠有情……”
苏国南喝了口水,淡淡笑道:“那你可知道老夫何以跟他结为兄弟?”
任行笑道:“大小姐喜爱漫游江湖,此事跟随大人的无一不知。如今有了这般俊秀、勇武又不失体面的江湖少年,又见大小姐处处含情,末将看得出的,大人自然也看得出。与他结义,一则是敬重他少年英雄,二则是不愿他与大小姐走得过近罢。”
苏国南静静听他说完,手中的水杯也似凝住了。
“任行,汝真知我也。”苏国南把水杯按在桌上,叹息道,“老夫虽喜欢这小子,但他终究是草莽中人。昨日张大人的话,想必你也听到了。话虽不中听,却句句是实。”
“正是。”任行道,“大人并非瞧不起他,只是不想把这掌上明珠,托付给一个四海为家的少年。”
“只是……上次把阿黎锁住,她还是想方设法跑了出来,这次,以后……老夫是担心,事情不会依着老夫想的走啊。”苏国南沉吟道。
任行道:“大人锁得住她的人,却锁不住她的心。这个少年侠肝义胆,其武艺末将昨夜也曾见过,比之几十日之前,似乎大为精进,料也护得大小姐。依末将所言,不如就纵了她去,莫锁得郁闷了。来日命运如何,也都是大小姐自己的选择。”
苏国南叱道:“你这厮多嘴!”
任行忙低头道:“末将不敢。”
苏国南道:“那依你说,老夫为何又骗他说把那些拳匪都杀了?”
任行笑道:“末将是说还是不说?”
苏国南道:“你说便是。”
任行道:“大人虽是奉诏平寇,其实大人心里,对拳匪起事,不知是对是错,该伐不该伐。捉得这些匪,虽本应解上京去,但大人内心也有疑虑,可是么?”
苏国南沉默不语。
任行又道:“大人骗顾少侠,似有故意与他为敌之意,是不想他再与大小姐来往。但大人心底,却还是喜欢这个少年,不忍从此分隔,故而末将把真相坦白之后,大人虽明知顾旸要前往半路相救,也并未再多说甚么。末将说得可对么?”
苏国南手指始终轻轻敲着桌子,听他说完,举起手拍了一下他的脑壳,大笑道:“你却心细,不枉你跟我多年,有话敢说。这些话想来吴信是不敢说的。对了,吴信方才如何不在?”
任行道:“吴信见苏大人在偏寨照料顾少侠,无人伺候张巡抚,他便给张巡抚倒茶去了。”
“啧!”苏国南打趣道,“这家伙却会溜须拍马!”
此时顾旸则已出了营寨,回到昨夜交战之处,只见偌大的丘陵之间,满地乱尸血肉,惨不堪言,各处停驻着乌鸦、野鹰,正这儿啄一口,那儿撕一片。
顾旸大怒,挥剑砍去,群鸟扑棱棱几声,扇动翅膀,都飞向同样血红的天空去了。
“是我害了你们。”
顾旸看着这遍地的惨酷景象,凝望良久,忍不住热泪便流出来,“扑通”一声跪倒在那一片血地里。
他只觉得两个膝盖还是微微烫的。
是的,有些人虽死,但血未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