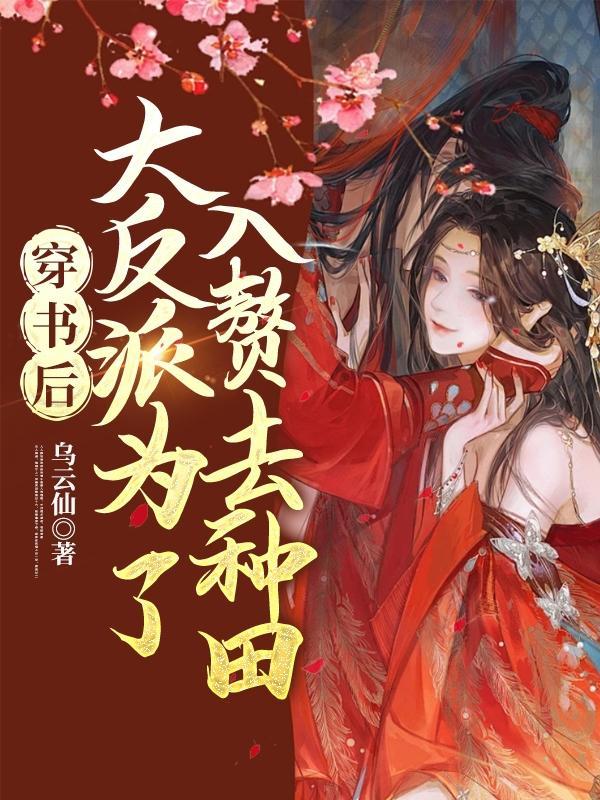看书阁>女子虎豹巡护队 > 第63章 神秘的新郎(第1页)
第63章 神秘的新郎(第1页)
窦芍药决定先从最普通的工作做起,然后厚积薄,伺机而动。
走出校门,就意味着失去了保护伞,意味着她此后要与家庭“断奶”,不再像窝里的幼鸟那样,张着嘴急吼吼地、理直气壮地等待父母的哺养。
她要自食其力了。
窦芍药先租了一间地下室,虽然潮湿阴暗,但租金便宜,没月只要7oo元。她把从学校带来的几个箱子安顿后,顺着台阶走出地下室,在旁边的馄饨馆吃了碗虾酱豆腐馄饨,就开始沿街寻找那些招工的小广告。
这些小广告招人,不是切菜工、传菜工、洗碗工、服务员,就是泥瓦匠、装修工人,再不就是伺候病患老人的。
前一类饭馆、酒店工作,她作为一个刚从重点大学毕业的大学生,正在踌躇满志的时候,还不到山穷水尽,心高气傲的她是“不屑”于应聘的。
而泥瓦匠和装修工人属于技术工种,而且基本属于男人的工作,不适合她。
而伺候患病老人和月嫂,属于家政服务行业,需要进行特殊培训,而且一般从事这个职业的大都是年纪四五十岁的妇女,她刚出校门有些不甘心。
连续两天没找到合适的工作,窦芍药有些焦虑,没毕业前他踌躇满志,以为自己重点大学的毕业生,肯定不会为就也愁,她那时踌躇满志的是,尽快毕业,尽快到社会上闯荡出属于自己的天地。
可是现实却像一盆冷水泼在她头上,她找不到理想的工作。
记得有人说过,以前经商年代,大街上十个人有九个人是经理,而现在是学习年代,大街上十个人九个是大学生。
大学生不金贵了!
第三天早上,窦芍药去了人才交流市场,手里拿着她昨晚熬了半宿精心准备好的应聘材料,走进大门。
她以为自己来得很早,可当他进入人才交流市场大厅时,这里已经人山人海。
到处都是手里拿着应聘材料的大学生,其中不乏名牌大学的研究生。
窦芍药大学读的专业是森林保护与病虫害防治,属于偏门,她转了一大圈,也没见到招聘“森保”专业的单位,屋里人挨人,拥挤、吵闹,熙熙攘攘,摩肩擦踵,像农贸市场。
窦芍药嗓子渴冒烟了,身上也挤出一层汗,脚底板隐隐传来疼痛,她挤出人群来到外面,买了瓶水,坐在花坛瓷砖上休息。
翌日,窦芍药不甘心,又去了人才交流市场,和昨日一样,除了挤出一身臭汗,脚底板走得生疼,嗓子说得冒烟,她仍没见到一家招聘“森保”专业的单位。
她不仅有些纳闷,现在国家的林业政策进行调整,不允许大规模砍伐,而是实行天然林保护工程,按理说她这样的大学生,是不愁用人单位的,或者说是被人争抢的“香饽饽”。
可实际情况却令她失望,她的所学是不被市场“认可”的,她似乎学了一个被人丢弃的专业。
晌午时分,窦芍药身心俱疲,精疲力尽,拿着一瓶矿泉水,郁郁寡欢地走出人才交流中心。
看起来,马志军的选择是对的,他曾说过,“我们所学的是什么专业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通过四年学习,获得了一个大学生的身份,而社会需要的,也不过是我们的这个身份而已,就像画皮里的那张皮。”
窦芍药想给马志军打个电话,倾诉一下心里的困惑和苦楚。
可电话还没打出去,她就放弃了这个念头。
她不能给他打电话,不然就证明自己的选择是错误的,他会更加强烈地要求自己回率宾县,跟他走相同的路。
她不想认输!她要再拼搏一把,她相信只要努力,成功的天窗迟早要对自己打开。
但是,她不想回率宾县也不行了。
昨晚好朋友扈红打来电话,邀请她回去参加婚礼。
“什么?你要结婚了?跟谁啊?新郎我认不认识?”
面对扈红突然的邀请,窦芍药差点惊掉下巴,问题就像一百头的鞭炮一样,噼噼啪啪。
“你别管我跟谁结婚,重要的是你必须回来给我当伴娘!”扈红跟她卖起了关子。
“快说,新郎是谁?我认识不?”窦芍药的关切点,却纠结于新郎是谁?
扈红就是不告诉她新郎是谁,说:“你肯定认识,到时你见了就知道。”
窦芍药没想到扈红会突然宣布婚讯,她记得春节回家时,她还没说自己处了对象,咋才半年多,她就要结婚了?看来,这个男人一定把她的芳心俘获了。
扈红没有考上大学,就跟着父亲和哥哥、嫂子一起,在自家承包的公益林里当护林员。
她跟窦芍药说过,不想再在林场干,她家承包的公益林是一座山场,几十公顷,属于原始次生林和人工林混交林,树木还没长成大树,就没有盗伐林木的,所以看护的任务不重,用不了她家的四个成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