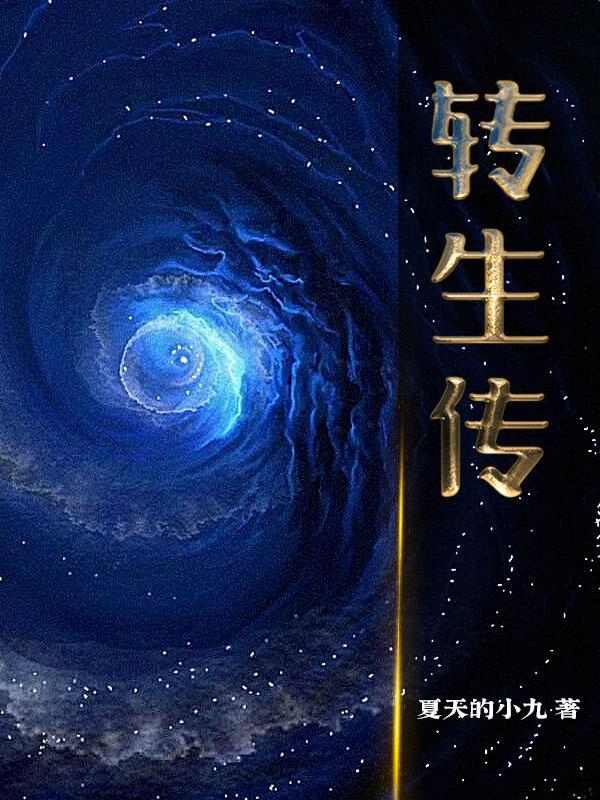看书阁>五代窃国 > 第一百三十二章 看风云闲暇度日(第1页)
第一百三十二章 看风云闲暇度日(第1页)
“中丞,书肆何必非要以国以营之呢?”张左耀德意思很简单,自然是以商营之,不过听在毋昭裔耳朵里,却不是那么回事!
只见毋昭裔皱眉以对,半响才回话:“中饱私囊之事,还是莫要再提……!”
“误会了,中丞,误会了!”张左耀一听这话不对味,赶忙解释:“末将的意思是,此学馆完全虽属朝廷,然,亦可以商理之。”
毋昭裔脸色顿时缓和不少,不过又一阵思考以后,他还是摇头:“一来,若大肆专营,恐怕那些士子不屑;二来,既有利往,难免多生枝节;反倒坏了这圣学之道。”
这话说来,到让张左耀有些郁闷,明明是件好事,却这么多顾及。想了好一会,张左耀还是觉得可惜,或许,他没有第二次说服这个最有能力实现这事情的人。
“中丞,请恕末将无理。末将是粗人,士农工商之高下我也道不明白;不过制书一事,末将到是有些想法!”张左耀说着,也不待人家同意,便滔滔不绝的说起来:“世间百事,什么事情做的人多,自然是有利可图的事情。即便杀人偿命,亦有人铤而走险,也皆因有利可图,书本凡贵重的,皆因其稀,而书少则因刊印繁琐,破费靡多而致;而眼下,活字印书,刊印只需排出版面,印一书看似与雕版之无异,但十书,二十书呢?”
“不过,这又有一问,若真印这么多书,刊印之费功劳力谁来担?造字工程比之雕版同样耗费,这个费用又是谁来担?中丞大义,为后之士子可以倾尽家私,然,中丞之后?再等十年?二十年?下一个中丞在何处?”
“所以,如果书在造书者看,如同柴米油盐有利可图,那么就必有营者;这就是不知书,也知书之利,最终,则活字必然可一套变二套,二变四,四变八。若天下之书皆可贩之,活字套件百千套,书,何愁不多?以书利可养书商,欲读书者亦能有书可读,这有什么不好?”
书的商品化当然不新鲜,然而,以往的书肆更像是现代的古玩店这一类,贩孤本,名帖,名家抄本等等。而张左耀此刻提出的,则是将书当饭菜买,这已经不止是贬低不贬低的问题,或许有些士人看来,这根本有些忤逆圣学之嫌。
但这也是事实,若是从一开始就考虑了利益关系,那么这个事业或许就不会断,会一直有人做下去……
“那,从造字开始筹措,耗费了如此多,如何收能回来?”毋昭裔沉默许久后开了口,似乎有些松动。
“这是可以慢慢考计的!”张左耀喜上眉梢,好像自己干了多大的事情一样:“从造字的成本开始算,多少匠人,耗费多少时日,每人每月的工钱是多少,这些钱肯定不少,所以才没有人愿意去做,只能朝廷支取,但朝廷没没为此事出钱财则或许会有损于国,所以,这笔钱必须要收回,这不是多少的问题,而是考虑今后可以出第二次,第三次,所以一定要有规矩,至于一年,两年,还是三年五载还上,就看朝廷的意思了。”
“那么字造成以后,刊印排版工人的钱,纸张费用等等看得见的成本则另算一套。书印一千本,买多少一本,既可以支付这些刊印的钱,也可以支付朝廷提供活字的钱,就是此书的造价,至于买卖……!”
调查两军大案的御史中丞全然不提案子,而领军在外的统军忘乎职责也不谈军事,却全都谈得性起,谈的入迷。你说奇怪,也不算怪,一个以此为志,自然关注,而另一个,常常着眼于利,有机会,总是不原意放弃,谁会嫌钱多呢!
……
八月初六。
暖阳旭日,漂浮的云确实比之污染严重的千年后更近,云后的湛蓝也确实更让人心怡。对于驻守天水关的蜀军来说,又是繁忙的一天。而对于张左耀,则又是一个新的等待。
毋昭裔走了。带着一抹子微笑和对张左耀期许离开的。他只告诉张左耀,一切有待圣裁,但只要他在秦州不然人失望,朝廷定不叫他失望。
这是个无比广泛的保证,却也是个让人无比坑分的保证,说起来好笑,张左耀直到送走毋昭裔和他的御林军骑兵护卫时还是不知道毋昭裔到底从那里关注到自己的。显然,这是在自己出征以前的事情。
唯一让人挺惊喜的是,数日前,胡三给张左耀写来一封信,报一报平安,讲了一下军镇的情况,也顺带着禀报了酒业楚大伯管理得很好等等。没什么大事,话里话外尽像是唠叨,但是,就是如此简单,但拿着信,张左耀德手却有些抖,情绪总难以平复,断断续续认字,结结巴巴读信,这让张左耀心理充斥着一种难以言表的亲切,让他体会到一种久违的牵挂,更让人觉察出一种让穿越者无比错杂的哀愁。
当然,回了信,一切本该恢复如常,但特旅却因为张左耀的一个小小举动而闹腾不已。那就是准许每个人写上一封家书,若家在南浦,则送至南浦,若不在,南浦军镇的袍泽也将负责将信送出,直到交到家人手中,包括那些新编入特旅的士兵。
这是个奇怪的命令,却在别真的实行以后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所有会写字的士兵,军官都被动员起来,几乎忙到手抽筋。许多战场上挨刀子都没有哼哼过的铁血汉子,写信那一刻却有的眼泪直流开不了腔,有的声音结巴嘶哑,有的像个女人一样揉捏自己的衣角。而那些其他部队的人,多数人都骂骂咧咧的表示不屑,但所有稍加注意的人都能从他们的眼力看到他们对特旅士兵的羡慕,看到他们对家人的思念。
当然,特旅这么闲,主要也是因为秦州雄武军的态度所致,占领天水关一晃多日过去,尽然没有任何一支成规模的部队赶来支援天水。而天水县乱了几天,在蜀军完全没有出关的举动以及本地闲散驻军相继赶到县城集结以后,也就安定了一些。除了直面天水关的南门,据说其他几门也都在白天会打开一段时间。
不过,随后的日子,天水又被张左耀惊下了一下,那就是他开始安排新军磨练。除了恢复行军战斗时停止的体能训练外,张左耀还安排了实战性质的出关巡视。从沿天水关向小川急行军简单任务开始,最后他直接要求以队为单位出北门巡视天水县城。
要知道,这是个十分危险的活,一歌队五十人,一旦被缠住,跑不了几个的。以至于个个出关都是小心翼翼,精神紧张。
而朝廷,这些日子以来除了一封责令张左耀暂领成州招抚使之责的招命以外,什么都没有。倒是一些关鸿大哥传来的消息更让人好奇。那就是兴州的战事真的越打越大了。
义宁军贺同梨老将军在得到张忠杰猜测凤州兵可能大举来犯以及兴州请援以后,派他的大儿子,也就是张忠杰的老上司贺继威领兴元府新编制的兵丁七千余驰援。而张忠杰自己则是召集兴州归蜀以后,由张左耀重新编制的所有可调部队到长举参战。
另一面义宁军的对手,一开始由唐任兴州刺史冯晖率领的河池兵则是直接搬来了凤翔节度使的一万兵马。浩浩荡荡的开进了冯晖的出地河池,正大肆囤积粮草,他们似乎随时都可能南下。若是再加上成州招抚军与雄武军的对峙,那么似乎,表象上看北方四州,全面开战了。
其实不止如此,接二连三的投诚与胜利,让蜀国内部充斥着一种好战情绪,调入洋州镇守的宁将军节度使张业大将混编改制好原孙汉韶部以后,偕同新任新任洋州武定军节度使全师郁虎视眈眈的望着兵弱马少的唐地金州。而自梁山之战逼降西方邺收拢东面芷州以后的五州镇府使赵廷隐将军,则是紧紧的盯住了更东面的前蜀之地,归州,侠州。
一切似乎都在等待,可是等什么,却没有人知道;一切又看似平静,内里却都充斥着的却是不安和躁动。这本就是个一日三变的年代,因为有了明宗孟知祥这样的人物才缓和了一些,而此刻,蜀王修养了百姓,也是培养了更多的士兵,恢复了农业,也就种出了更多的粮饷,这是个多么讽刺的现状,也是个让人多么无奈的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