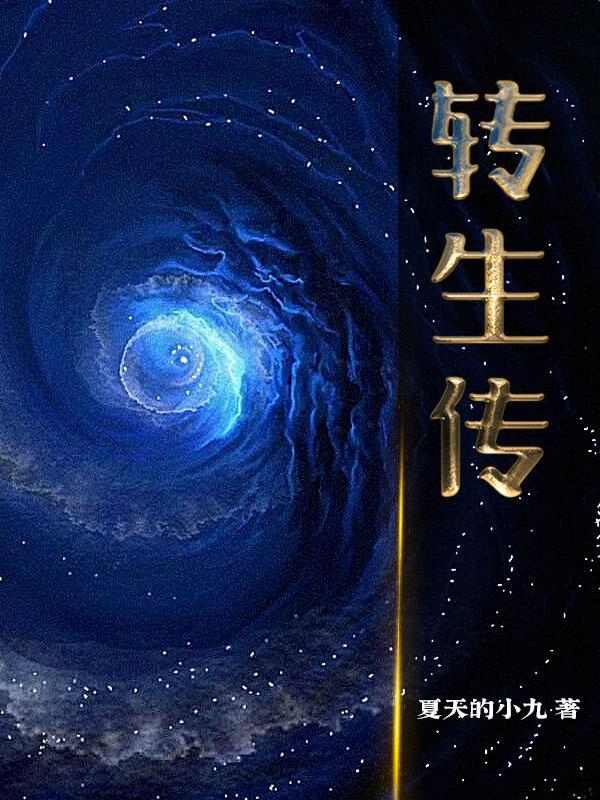看书阁>掉进虫巢成为虫母 > 第135章 虫体与蟋蟀(第1页)
第135章 虫体与蟋蟀(第1页)
好一会儿,薄翅螳螂、解红沙与天牛一阵静默。
蟋蟀凑近看,逼到她们近前,“一个会用针的也没有吗?”
还是一阵静默。
“没用,没用,真没用啊”,蟋蟀抓脑袋,“这样,至少得5天才能学好!你们三个给我一起学,谁学得快就学完,学得慢就淘汰!”
蟋蟀从案桌后拿出一卷蛇蜕,铺展开,各类虫族的口器排列其上,有长有短,有粗有细,或闪烁金属光泽,或柔软卷曲。
它从里面拿了一根口器,下端无比细长,上端开了朵喇叭花,“这就是回钩针了”,它拨了拨口器最下端小小的弯钩。
蟋蟀在一只虫体上直接操作,肢爪按住胸腔,回钩针猛地插进一根起伏血管,药液从喇叭花处吨吨灌入,虫体呛醒,“该死的,你又在我身上做演示。”
说完这句,虫体又睡了过去。
解红沙、薄翅螳螂与天牛悄悄地各自后退一步,好可怕啊,这个医师。
蟋蟀掀开一片卷曲树叶,埋进里面翻翻找找,各种口器碰撞出清脆声响,它从里面摸出三根回钩针,“你们用这些练习,就在这只虫体上,它是活死虫,又是僵尸虫,没有知觉的,一天只清醒片刻,它醒来喷的话你们就当没听见好了。”
蟋蟀开始讲每一步的细节,接着就留给解红沙她们自行练习,它旁观一会儿,眉头越皱越紧,越皱越紧。
解红沙又有了当年被夫子压着背功课的紧张感,手一抖,回钩针穿透虫体血管,蓝色血液大面积浸染开来,但虫体没有醒。
片刻后,蓝血停止流动,自动回缩,血管恢复原样。
蟋蟀走了,一路嘟囔着“爪子真笨哪,真笨哪……,完蛋了,吹嘘什么一定能把它们教会,讲什么大话啊……。”
解红沙与小虫们彻夜练习,第二天蟋蟀来看,虫体全躯肿得老高,脓包透亮,这得被扎多少下才能这样啊。
“我们通宵练习了,现在已经可以完美扎进血管”,解红沙与小虫们眼睛亮晶晶等待夸奖。
中间虫体醒过,但薄翅螳螂立刻就用蛇蜕封住了它的鄂,没叫它说出什么不讨喜的话来。
蟋蟀摸上高高的脓包,满目心疼,“你受累了,我的老伙计。”世界上最可怕的,莫过于蠢笨又勤奋的学师虫了。
“等它恢复好了,你们挨个扎给我看”。
虫体悠悠醒来,听到的恰好是这么一句,它瞪大眼睛,用眼神大声而激烈地辱骂着蟋蟀。
“我们得保留它泄的权利”,蟋蟀松开蛇蜕。
整个白巢瞬间充斥着各式各样、不同语言、无一句重复的咒骂。
虫体修复时间,解红沙与小虫们继续回到药房,拿出虫师的书籍与部落虫们的树叶片给药虫看,药虫翻了翻,爪子动得很快,“这个有,这个有,这个有,这个也有,这个也有……等等,这个没有。”
药虫抽出一张树叶片,树叶片上一只九头小花,很是可爱娇俏。
“这种药很难找?”解红沙接过树叶片,当时给树叶片的虫族太多了,她有点想不起来是谁给的她。
药虫摇头,“不难,只因为它是只能治疗一种病症的惰性药,所以我们这里的常备没有它。明日有药虫上山,我们给你们带几株回来。”
“好的,谢谢,多问一句,这药针对的是什么病症。”
“软骨。”